
张威,1983年出生于沈阳,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脱口秀俱乐部创始人;原创民谣歌手,专辑有《狼北方》。
讲述 张威
主笔 团团
这是我第二次逃去日本。第一次是19岁,而这一次,我已经33岁。
离开北京时,我一无所有。我甚至想好了,这次去日本,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碌碌一生。
经历一次又一次失败,梦想什么的,已经跟自己无关。文艺的梦,就做到这吧,该醒了。
我像条丧家犬般,走在日本繁华的街上。人来人往中,只有我一个失意的身影。
这一整条街都是卖乐器的,我读书时常常独自来逛。
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着我来到这里。
不知不觉中,我迈步进一家装潢老旧的小店,墙上挂着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中古吉他。
有一把和我年龄相当,是80年代初的morris老吉他,成色很好,价格也合适,我一眼看中了。
半夜,在小单间的榻榻米上,我抱着老吉他开始换弦,调弦,磨琴桥、琴枕。房间里灯光很暗,安静得只能听到琴弦被拉紧时发出的“嘣嘣”声……
一个念头冒出来:如果在之后几十年的无聊生活里,能弹弹吉他解闷,也是好的。
就像当年的父亲一样。
 我和父亲
我和父亲
01
从幼儿园开始,我就住长托了,一礼拜回一次家。
父母总是吵架、砸东西,父亲甚至会动手打人。

记忆里最美好的画面,是停电的夜晚。
家里点上蜡烛,在微弱、摇晃的火光下,父亲拿出他的老吉他。
他其实不太会弹吉他,每次停电,都只能弹出一段简单的旋律——来自一首俄罗斯的曲子。
黑暗中,烛光把父亲的脸映照得红彤彤的。他笑着问我,还想听什么曲子?
“小星星!”小小的我,只知道这首歌。
“好。”父亲抱着吉他,很认真,在第一根琴弦上,一个音一个音地弹着……
02
13岁,父母离婚。
母亲一个人离开家,离开沈阳,去了日本。之后很多年,我们再没见过,只有我过生日的时候,会收到她托人捎来的礼物。
从幼儿园到小学四年级,我学了6年书法。

我挺喜欢音乐的,问母亲,为什么不送我去学钢琴,她说,钢琴多贵啊,学书法便宜。
童年里,父亲的老吉他就是我的玩具,我时常抱着它,胡乱拨出几个音。
这把老吉他当过仓鼠的笼子,翻过来就是我写作业的小桌子,它也是我和表哥打架时的武器……
初中,我开始疯狂着迷Beyond乐队,迷恋到自己用水彩笔在家里的白墙上涂鸦了“BEYOND”六个大写字母。

有一次,学校文艺汇演,我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
选节目时,我抱着父亲的老吉他,上台唱了一首beyond的《AMANI》。
教导主任跟我说:“你唱得不错,就是这个弹吉他的声音能不能再大一点?”
“老师,真的不能再大了,我已经很用力拨弦了……”我一边极力解释,一边使劲地用拨片去刮最上面的那根弦,都快刮断了。
最后,没能选上,我挺伤心的。
03
初中毕业的暑假,我和父亲说想去学吉他。
父亲同意了,他给我买了一把新吉他,220块钱,吉他课的学费是150块。
第一节课,吉他老师说,我们今天学一首歌《痛哭的人》。
“一下午就能学一首歌吗?”我惊讶地问。
“没问题的。”老师笑着说:“好,我们先来弹第一个和弦……”
看老师演示,我完全傻掉了。原来还能两根弦同时按?我从来不知道。
父亲弹吉他只有单音,我也就认为吉他只能弹单音。原来和弦的声音可以这么大,而且有这么多旋律……
这一刻,我突然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文艺汇演落选。

跟着老师学了一个多小时,整首歌我都会了。
我气冲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展示:“我给你弹首歌,叫痛哭的人,你听着。”
看我表演完,父亲点点头说,弹得挺好。
我扬起下巴,轻蔑地对着父亲说:“这才叫弹吉他,你懂吗?”父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做饭去了。
“如果不是你什么都不会,我就不会弹得这么烂,哪怕你会弹一点点的吉他,多教我一个和弦,那次文艺汇演也不会落选了。”我心想。
少年时期的我,打心底里责怪父亲,甚至有点儿瞧不起他。
04
高中时,我在班里组了个乐队,就叫“高三6班乐队”。我们四个人,一个吹长笛,一个弹键盘,一个弹华彩吉他,我是主唱兼吉他手。

我经常用父亲的老吉他练习弹唱,甚至想在上课的时候也练练吉他指法,但是这把吉他太大,没法带去学校。
于是,我把父亲的老吉他,锯断了。剩下的琴箱,被我一脚踩碎。
咣……重重一声,琴弦断了,老旧的木料碎得四散纷飞。琴把锯断之后,上面没有琴弦,它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我拖着老吉他的残骸,出门,下楼,抬手往垃圾堆里一丢。它落在一堆五颜六色的垃圾中间,和它们一样破破烂烂。
几天后,我一边弹着新吉他,一边随口跟父亲提起:“你的老吉他我砸了,它太烂了。”
“好好的,砸它干什么呢……”父亲看了我一眼,居然没有骂我,甚至没有发火。
“反正你也不弹,丢在柜子里积灰。我弹着不顺手,声音太差,不想要了,还是新的好。”我拨弄着新吉他,头也不抬地说。
父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做饭去了。
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没人再提。我以为它在我心里也就这样过去了,许多年,我都没有想起一次。
日子过得太快了,我一个劲儿往前跑,来不及回头看。
05
高中毕业,我想出国留学,打定了主意要去。
父亲说出国读书太贵。我说我自己打工赚学费,不花你一分钱。
青春期的我和父亲“水火不容”,没说几句话就能吵起来。
换个环境,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改变吧。
去哪里呢?第一个出现在脑海里的国家,日本。
嗯,妈妈也在日本,说不定能找到她。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她了。
我准备边打工边读一年语言学校,再考大学,目标是早稻田大学。
坐在飞机上,看着沈阳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我暗下决心:终于离开这儿了,我一定要在日本混出个样子来,给你们看看。

2002年10月7日,19岁的我独自前往日本。
到横滨吃的第一顿饭是房东请的,吉野家最便宜的牛肉饭。
刚到这儿,我觉得日本什么东西都贵。我和另一个女孩,不约而同地把盛牛肉饭的泡沫碗用水刷干净,准备当作平时吃饭的碗。
它一直在柜子里,没用过。半年后搬家时,我收拾东西,一打开橱柜,看到这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碗,心里五味杂陈,差点哭出来。
06
我们的宿舍在横滨的郊区,出车站,还要走路翻一个小山坡,走上20多分钟才到。
我们这个“寮”(宿舍)是一座日本民宅改建的,原来的屋主破产了,房子被中国房东收来做留学生宿舍。
10几个人住在一个“寮”,两个人睡一间卧室,上下铺,厨房、客厅、卫生间和院子是共用的。
我白天在语言学校上课,晚上就自己找地方打工,人生地不熟的我日语也说得不好,我连找了几天都没结果……
大家经常为一个职位抢得“头破血流”。我问了一圈才知道“内幕”,留学生想找到工作,有时还得给中介塞钱。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刷碗,在一家叫“金临门”的香港料理店,它位于横滨市中心一座摩天大楼“yokohama sky”的顶层。
刷碗工一小时的薪资是760日元,相当于60多元人民币。
我每天4点半下课,6点前赶到餐厅,一直干到晚上11点,再坐地铁回宿舍。
跟你们说一件很好玩的事。
这家餐厅里最贵的菜是烤鸭,但其实是“假烤鸭”,只是用大油锅炸了一道,根本没烤。因为店里根本没有烤炉!
“炸鸭子”由服务生端上去,在客人面前片好,他们只用鸭子背部的一小方块肉,包成4个鸭饼,其余部分就端走,直接丢掉。
我觉得太浪费了,问后厨的人能不能把鸭子给我,他们欣然同意了。
于是,我每天下班拎着两只鸭子回家。左手一只鸭,右手一只鸭。
我上铺的大哥之前做过厨师,每回他从我手里接过鸭子,都要笑嘻嘻地说一声:“您辛苦了。”
日本的肉很贵,大家都不舍得买,而每晚带回免费鸭子的我,被他们尊称一声“鸭哥”。
深夜,一屋人子围着刚出锅的热腾腾,冒着肉香的鸭子大快朵颐,真是太满足了。
07
10月来到日本,一晃就进入了横滨的冬天。
这里的气候和沈阳完全不一样,有属于沿海地带的温暖、潮湿,难见积雪。
1月,快过年了,来到这里三个多月,我有点儿想家。
大年三十在宿舍里过的,一帮人闹哄哄的,做了不少菜。
这天晚上,其他人都接到了家里打来的问候电话,唯独我没有……父亲明明有我在日本的号码。
这个年过得挺冷清的,还是一样每天上课、打工。
之后给父亲打电话,才知道他是搞不清怎么打越洋电话。别的父母都能学会的事,为什么偏偏你就不会呢?打一个电话,问问人,就这么难吗?
一堆埋怨在我心里堵得慌,像系上了一个死结,很多年都解不开。
08
为了自己赚够学费,我开始拼命打工。
第二个打工地点是一家“现象所”——洗胶卷的工厂。工厂在偏僻的郊区,坐电车去要一个多小时。
我的工作时间是晚上6点半到凌晨2点。因为赶不上最后一班车,我只能在厂里呆到早上。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操作一个大机器,把胶卷放进去,再等着照片洗出来。
工厂很大,夜里有上百人在工作,大多是中国人和斯里兰卡人。
凌晨,住在附近的人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在休息室坐着,有时也在卡拉OK里呆一整晚。
第二天一早,我掐着点坐第一班电车回去,补个觉就赶去学校上课。
这还不是最疯狂的,考大学前一年,打了一年的夜工。
我找到一份罗森便利店的夜班工作,每天晚上9点干到第二天早上7点,一周6天。
在店里值通宵夜班,没地方睡觉。一般12点之后就没什么客人了,我趁着夜里的时间看书、刷题。
早上下班,回家睡一会,紧接着要坐一个小时车去学校上课。下午5点放学后,再眯一个小时,就得赶去便利店上班。

这一年里,我每天睡觉的时间不到4小时,脸色很苍白,黑眼圈重得吓人。
我和父亲两个月通一次电话,他一直以为我在日本过得很好。
可他不知道的是,我每天光给人鞠躬就要上百次。到了夜里,腰和脖子都疼得要爆炸了,腿又酸又麻,眼睛也累得睁不开……
我不想父亲担心,再苦再难,一个人咬咬牙就熬过去了。既然出来了,就要拼命混出个样子。
09
2005年1月19日,我收到了早稻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教育学部。
为了这一天,我用心准备了整整两年半。

其实我也不确定自己能考上,但读不了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而且签证也快到期了……
为了在日本活下去,我没有退路,只能放手一搏。
考上早稻田,父亲是以我为荣的吧……如果母亲也能知道这个消息就好了。
发榜当天,我刚下夜班,连宿舍都没回,直接坐车到早稻田的校园。
教育学部前面立着一个告示牌,我挤进人群去看发榜结果。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金榜题名。
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很快褪去,迎接我的是开学的第一笔费用“90万日元”,包括半年的学费和入学金。
交完钱,我全身上下只剩1000日元了,而距离下一笔兼职工资入账还有10天。
幸好,我在宿舍囤了很多吃的,靠存粮饿不死,也能捱过10天了。
我每天都会去宿舍楼下的ATM机查询卡上的余额,数字一直显示是1000零几块。我不敢再提款,这我最后的财产。
直到第四天,我突然看见屏幕上显示“19800”,以为自己眼花了。
我又定睛一瞧,原来不是“19800”,是“198000”!
哪里来的钱,怎么可能?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我一次性把钱都取出来了,高兴了半天,但不敢乱花,总觉得是某黑帮的诈骗,之后要敲诈勒索我……我只买了一点零食和饮料改善改善生活。
4月,开学后的第三个月,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早稻田大学的邮件,上面写着:因为你入学成绩优异,所以我们将入学金的一部分退还给你,作为奖励。
原来是奖学金,而且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是我自己做的……
在早稻田的四年是快乐且自在的。
打工之余,我参加了学校的搞笑社团,开始表演小品。
大二和大四时,我报名参加了日本的喜剧综艺选秀比赛。
我一个人演过日式幽默短剧,也两个人演过漫才,虽然海选第一轮就被淘汰,但都是很有趣的尝试
空闲时,我会去看线下的喜剧表演,也喜欢去街头,看日本音乐人唱歌。
喜剧和音乐有一种共同的魅力,让人沉浸,也使人放松。
10
2009年4月,在“三菱重工”专属的温泉度假村里,我和近100个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一起参加入职典礼。
除了包括我在内的两三个中国人,其余都是日本各地来的优秀年轻人。
庆祝宴上,大家在一起碰杯,他们高声大喊:“接下来的30年请多关照!”
说实话,我吓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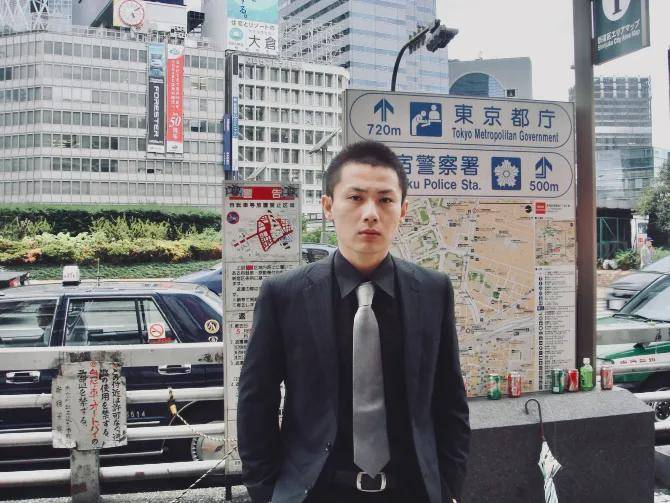
三菱重工作为日本知名企业,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大厂”“顶流”。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考上好大学,就是为了找到这样一份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一旦入职,就要“效忠”企业一辈子,他们从没想过自己还会离开。
这个工作确实不错,但我不能确定自己会干多久。难道从此刻起,未来的人生就一眼看到头了?我心里有点发毛。
三菱重工在东京品川有一幢摩天大楼,和其他几个日本著名企业共占着这一块商业要地。
我所在的部门是做大型压缩机透平机的,虽说是“部门”,但它实在太大了,算上地方的工厂,各个环节的人,得有几千人。
而我只是众多“螺丝钉”里的一个,负责中国大区的销售对接。
下班后一个人的夜晚,我时常在家自弹自唱,许多孤独寂寥的日子是音乐陪伴了我。
但我也知道,自己的歌唱得挺一般的,也许“说话”和“搞笑”更适合我吧……
11
日本的经济愈加不景气了。
2010年夏天,整个部门从东京撤出,调回到广岛地方工厂。
我一时间难以适应,这么多年来积累的人脉,东京多彩便利的生活,多元的活动,还有女朋友……都离我远去了。
广岛的太阳很毒,我穿着背心走在路上,汗珠都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变得滚烫,滋滋作响。
工作是枯燥无聊的,下班之后,我除了逛超市,就是在公司的社员寮里用PPS看节目,正值中国的《快乐女声》开播。
这时候还没有微信,日本的“小春论坛”我经常玩。
上面有一个人发帖子说:现在国内怎么了,“快女”里有一个叫“曾轶可”的,唱歌这么难听,居然还这么火?然后粘贴了几首歌的链接。
我点开之后一听,虽然不能说唱得很好,但作曲确实有自己的风格。
我回帖子支持她,遭到很多网友的围攻。
不过,看到节目里这么多年轻人上台唱歌,勇敢展示自己,我挺羡慕的。
节目看多了,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也能去试试……
12
之后的一天,我听说了一个消息:有个新社员从宿舍6楼跳下来,自杀了。
尸体被很快抬走,连血迹也清洗得干干净净。
我和他不是特别熟,甚至没说过话,只知道是和我同期入职的。在入职的庆祝宴上,也许我们还一起碰过杯……
追悼会上,我们去了200多个人,大家都穿着黑色西装,沉默不语。
逝者的父母和弟弟坐在棺木的旁边,一直低声啜泣。
走出冰冷的殡葬大厅,外面的太阳还是一如既往地毒辣。没一会儿,汗水便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我西服里面的衬衫很快湿透了。
我突然觉得浑身上下疲惫不堪,有一股冰冷的东西在体内散开,不禁打了个寒战。
只能选择死了吗?如果不死的话,还有很多可能的吧,为什么不再试试呢?
这突如其来的“自杀事件”就像一个“暗示”,不断在我脑海里盘旋。
就在这个酷热的夏天,我下定决心从三菱重工辞职,回国。
离开广岛之前,寮长叫住了我,他疑惑不解地问:“你确定要从三菱重工辞职吗?”
他的潜台词是:这么好的工作,怎么会有人想离开。
我点点头,笑着对这位满头白发的日本老三菱说:“我要回中国,去追梦”
13
2010年冬天,我在北京首都机场下了飞机,一个人背着两个大包,推着巨大的行李箱,还拎着一个提包。
走出机场,我用力吸了一口北京的空气,冰冷、浑浊,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从2002年10月独自去日本留学到这一天,八年里,我是第二次回国。
第一次是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沈阳老家看望亲人。
五年多不见,父亲又老了许多,但脾气还是一如既往,几句话,我们爷俩就能怼起来。
我一个人悄悄去了大舅家,凭着儿时的记忆,找到了他们家的老房子。沈阳都拆得不像样了,我差点迷路。
一开始敲错了门,邻居说是旁边那栋。
进了大舅家,我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还留下在日本的电话。我和大舅说:“如果母亲愿意联系我,就让她打这个电话吧。”
大舅的表情有点犹豫、迟疑,他们一直和母亲有联系,但不愿意告诉我。
是怕我给母亲添麻烦吧……相比我这个侄子,他更需要保护自己的妹妹。
回到日本后没几天,我就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我们在东京见面,她说自己一开始来日本也吃了很多苦,后来一边打工一边慢慢扎根,现在又成立了新的家庭。
母亲的样貌和我记忆中的模糊印象缓慢重叠,最后变成了如今的新样子。
小十年没见,我们母子俩都有点拘束,不知所措。
我和母亲说,我在早稻田上学,一切都好。
母亲笑了,欣慰中透着一丝尴尬,尴尬中带着一丝无奈。
最初选择去日本留学,也有母亲的原因,19岁的我懵懵懂懂的,只想着逃。
一个人逃离,一个人打拼,一个人在日本站稳脚跟,然后,又有了新的生活……我们母子俩的路,何其相似啊。
但这一次,我是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意愿回国的,虽然身边人都极力反对。
相比平静如水的日本,中国有浪,一股接一股的大浪。我也想乘着这大浪,任性地追一回梦。
14
我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BON蓝海电视台做实习生。

我想自己做一个英文脱口秀节目,名叫“Panda Panda”。
一个人窝在摄影棚里写稿、录制、剪辑,我满心想推出一款自己的作品。但最后这个节目直接被台里毙掉了,自己确实能力有限。
不久后,我去参加了北京卫视的一个求职选秀节目“勇闯娱乐圈”。
在舞台上,我一个人表演了几个日式小短剧,评委们都很喜欢,我入选了。

终选环节,我面对的两家公司分别是“开心麻花”和“光线传媒”。
我毫不犹豫选择了电视行业的“大佬”——光线传媒。满怀欣喜,我以为自己入职了传媒界的“天花板”,未来定是前途似锦,风光无限。
看着公司墙上的一众娱乐节目主持人:谢楠,柳岩,大左……我梦想着成为他们。
但我还是太幼稚,对这个行业根本一无所知。

一整年时间里,我只是明星访谈节目“最佳现场”的一个边缘人员,坐在角落里,镜头很少。
我不是主持专业出身,只能偶尔吐槽几句。很快,我被“无限期冷藏”了。没有节目,就没有工资收入,我像一个顶着“光线传媒”光环的无业游民。
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深深的挫败感。
15
闲来无事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北京的线下脱口秀开放麦。
由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组织,在鼓楼东大街一个中老年的活动室里,因为场地免费,屋子挺小的,只有十几平米。
老年活动室里零零散散摆着五六张椅子,前面是一个直立着的麦克风。主持人介绍完,大家就轮番上去讲自己的段子。
观众两三个,演员五六个。第一次上台时,我抱着尤克里里上去,边唱边讲,场子很尬。
但喜剧我是发自内心喜欢的,我是一个“表达欲”爆棚的人。
自己在家的时候,会忍不住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半夜想到一个好玩的事儿,也会马上跳起来,对着镜子“吐槽一番”。
体内好像有很多能量需要释放,有很多话想说给人听。喜剧和音乐,是我仅有的“出口”。

16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我开始频繁参加各种选秀节目。
2013年,我去参加山东卫视的“中国星力量”,边弹尤克里里边唱了一首英文歌。
评委是瞿颖,她委婉地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相信你做其他行业也可以很好。”
太婉转了,婉转地像一把刀子。
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似乎总有一团火,在身体里上蹿下跳,发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我又陆续参加了“黄金100秒”“快乐男声”“星光大道”等比赛。
在“星光大道”现场,我注意到一个中年男子,他拽着一个大行李箱风尘仆仆地赶来。
海选上,他拿着自己的葫芦丝和二胡,演唱了一首民歌。他跟评委说,上星光大道是他一生的梦想。
但评委只有冷漠的一句答复:对不起,你没有过。
下台后,我走过去跟他聊天,他说是江西人,现在在贵州电力系统工作。这边表演结束,他连夜就要坐火车赶回贵州上班。
他快速收拾完自己的乐器,扛起大包,满头大汗地离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内心深处被触动了,这是一个多么失意,又落寞的背影啊……
可我没想到,这个失意的背影,在之后的日子里,会无数次在自己身上重演。
17
最后一次参加唱歌选秀比赛,是在北京卫视。
初赛,我表演了一段喜剧RAP,观众的反应很热烈,我PK掉了另一个专业歌手。
评委是戴玉强,他对我说:“我觉得你具备了所有流行歌手要具备的素质。”
第二轮,我唱了一首张学友的歌。有几个高音部分我都是用嗓子喊上去的,也许是评委发现我没专业学过唱歌,我被淘汰了。
所有这些比赛,我都觉得力不从心。
之后,我离开北京到苏州电视台工作,做了一档节目叫做“乐活六点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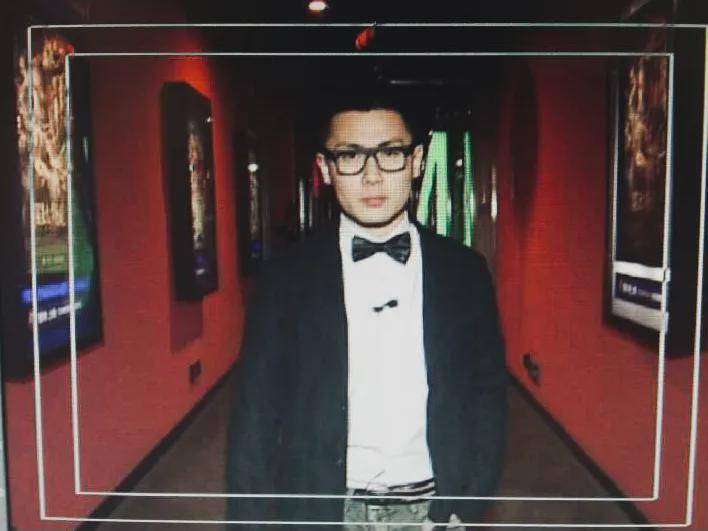
在体制内上班,与我的脾气个性格格不入,我时常因为一些想法和领导争执不下。
2014年9月,我辞职了,离开了苏州。
原本来这儿的时候,是来“圆梦”的,一个正式做主持人的梦。
原本在这儿,我甚至想过结婚生子,就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定居,安安稳稳一辈子。
如果我不辞职,留在苏州,应该可以做一辈子的梦,因为,梦已经实现了不是吗?
离开的这一天,苏州下着瓢泼大雨。傍晚五点,天灰蒙蒙的,我没带伞,背着两个大包,还拖着行李箱。
到车站时,我浑身都湿透了,人和行李都不断地往下滴水,狼狈不堪。
江西男子的背影又出现在我脑海中,都是失败的追梦人,我们没什么不同。
许多人都劝我,能得到一份编制内的工作不容易,别人挤破脑袋都进不来,你却轻而易举地就走了。
我真的是一个很任性,又很鲁莽的人吧。我发现这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除了离开,我想不到该如何凑合着过下去。
还是太年轻了。

决定回北京前,我接到了“开心麻花”的邀请,他们想和日本的娱乐公司联合做一档节目,要找一个会日语的演员,刚好就想到我了。
我觉得这简直是“天意”,要召唤我回到北京。但在北京等着等着,最终等来的消息却是“这个项目被砍掉了”。
晴天霹雳。几个月的等待付之东流。我发现自己对文艺圈真的一无所知,我真的太傻,太天真了。
想起一句歌词:“我曾满怀希望也满怀悲伤等到天亮,我曾豪情万丈又失落迷茫没有方向。”
我心灰意冷,跟自己说,到此为止了,再也不碰这一行。
又和朋友做了一段时间生意,亏光了老本,我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它们都快溢出来了。
心灰意冷,我决定去日本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结婚生子,碌碌一生。这就是未来的打算。
18
2016年6月,33岁的我走在日本的街头。是的,这一次,我又逃来了这里。

当时在日本找了一家小公司上班,下了班没事,就去听街边的歌手唱歌。
在横滨靠海的地方,有一个车站叫樱木町。站前有一个广场,这里总有乐队在演奏。他们唱着自己原创的歌,顺便卖自己的原创CD。
在这里,大家都要靠自己的作品说话,很少有人翻唱别人的歌,他们都盼望着有一天自己的好东西,会被人欣赏。
这里没有输赢,没有名利,也没有竞争,人们只是享受音乐,享受它的陪伴和治愈。
看着他们卖力的演唱,我也想起了高中组乐队的那段日子,可我分明已经很多年没有碰过吉他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当年砸坏父亲吉他那一幕,经常浮现在脑中,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当年我砸坏了他的吉他,那就再给他买一把老吉他吧。
自从买回这把老吉他,我一发不可收拾,在日本旧货网站上淘各种各样的老吉他:60年代的铃木,70年代的雅马哈,1875年的德国古典琴……

可这些琴都是日本琴,都不是当年陪伴父亲长大的那把破国产琴——它虽然破,却承载了父亲青春时期的记忆。
也许,父亲根本不在乎那把吉他……
我曾对父亲旁敲侧击地询问:“你平时还弹吉他吗?你还记得以前那把吉他吗?”
他回答的时候,仿佛在寻找一段遥远的记忆,看他的神情越迷茫,我心里的负罪感就越小。
有一次回沈阳时,我无意中走进了一家饭馆,这家店只卖炖牛肉米饭。
饭馆的装修很复古,堆满了80年代的录音机、电视机、毛主席像章、缝纫机,居然还有一把破得不像样子的老吉他。
店主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我问他那把老吉他是谁的,他说是他儿子的。
“你儿子现在还弹吉他吗?”我问。
“早就不弹了,就他上学的时候玩了一阵子,这不都放在这里当摆设了。”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阵释然,我最害怕的是当年砸碎父亲的那把老吉他,会不会就彻底断送了他的音乐之路?如果我没有砸碎他的吉他,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汪峰?老年版的……
想到这,连我自己都觉得离谱了,父亲怎么会成为老年版的汪峰呢?他连和弦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至少,我也剥夺了一些属于父亲东西……我想试着补偿回来。
“你还记得以前那把吉他是什么牌子吗?”我问父亲。
“翠鸟!”不到3秒钟,父亲就干脆地答了出来。
这让我非常惊讶,砸吉他的事已经过去了快30年,他是怎么一口答上来的?
知道牌子,我想在闲鱼碰碰运气,一搜还真有,而且出品地几乎都是辽宁沈阳市附近。
这就对上了,70年初,中国做吉他的厂子就那么几个,在东北那边的厂牌,就叫“翠鸟”。
翻了半天,有一把“翠鸟”映入眼帘,和父亲当年的那把是一个款式。它已经坏得不像样子,我价都没还,就买回来了。

我怕弦太硬了,拉坏了这老身子骨,又换了一套超低张力的弦。拿在手里,我拨了个和弦,嗯?不对。
我又故意把琴弦胡乱松了几度,再拨,嗯,对了!这才是当年那把老吉他的味儿。
因为,父亲是不会调弦的,他的弦,从来就没准过。

19
老吉他的美好,小时候的我不懂,但现在,我好像渐渐懂了。
无论是走在街上,还是宅在家里,只要脑海中有旋律荡漾,我就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然后用吉他反复弹奏,琢磨里面的节奏和乐感。
断断续续的,我在语音备忘录里留下了几百条旋律。它们都是我原创的,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有感而发。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关于音乐的一切,隔了这么多年,正在回归。

第二次回日本上班的时候,我最大的娱乐就是宅在家里玩游戏。游戏过程中,我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看着队友一次次为我献身,保我不死,场面可谓壮绝激烈。
赢得比赛之后,我情绪激动,潸然泪下,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正好看到手边那把70年代的老日本古典吉他,随手拿起来,就弹奏出了我的第一首原创歌曲“苍风吟”的主旋律:
“多少人来到北方 不再追求 热泪盈眶,
我站在 红土衬葱茏 狼的北方 ,
苍风青 长城长 黑牛间白羊,
丝路接远疆 叹北风狂掀黄河巨浪,
七海八疆皆孤独 星野尽苍茫,
大漠映昆仑 隔离北方于尘世喧嚣啊,
桃源乡格桑旁 和你席地而唱,
天圆地方 东海浩荡 看潮落潮涨 ,
你肉身何处安宁,灵魂在哪安放……”
这首“苍风吟”的词曲都是我自己创作的,我把它收录进专辑《狼北方》。
我还计划创作20首歌,作为自己的第一个原创作品集。这20多首歌连在一起,讲述的是一个战争故事的不同阶段,用音乐描绘两个部落在荒原之上的大决战。

20
也许,真的有一种东西叫“蝴蝶效应”。
从儿时砸坏父亲的的那把老吉他,到我的音乐之路,每一步,都有迹可循。
第一首歌的成品费尽周折出来的时候,我欣喜若狂。
但当我把歌发给父亲的时候,只打了几个无声的字:这是我写的歌,听听。
他说我的歌很好,他喜欢。
父亲年轻时,也是有过“音乐梦”的吧。
奶奶说,父亲初中毕业之后没事干,她怕父亲学坏,就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和一身蓝色运动服。
那把“翠鸟”吉他花了奶奶一个月的工资。父亲闲着没事儿就穿着蓝运动服,抱着吉他站在家门口拨弄。
我没跟父亲提我淘老吉他的事,也没告诉他我买了一把70年代的“翠鸟”。

只是有意无意的,我问过他一次:“你还记得我砸你吉他的事吗?”
父亲说,忘了。
那把老吉他也曾是父亲的慰藉吧,我在真正喜欢上音乐,喜欢上弹吉他之后,才知道琴的意义。
它陪伴了我这么多岁月,怎么能没有感情。
它曾陪伴了父亲那么多岁月,又怎么能没有感情。
父亲是个念旧的人啊,家里的老冰箱用了几十年都不舍换。
吉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件物品吧,只是它承载过的青春记忆,我不得而知。
我像“赎罪”般地不停收集老吉他,似乎当年那一砸,让父亲失去了琴,也剥夺了他的热爱。
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呢?好好做音乐,用心写出好歌,是我唯一的方式。

一切都像老天爷设好的局,他让年少无知的我砸了父亲的琴,又让中年追梦的我,再次踏上音乐之路。
我的每一首歌,每一句词,每一个音符,都像曾被深埋的种子,经历了无数风雨,才一点点萌发,破土,终得以见光。
现在,我的原创专辑《狼北方》中已经有五首歌:苍风吟,啸天歌,龙狼谣,梦咿呀和君出塞。
从第一首歌的诞生,到创作完成第五首,一晃五年过去。填词、编曲、混音,每一个细节我都无比用心对待,它们就像是我的孩子。
21
2017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这是第三次入京。
只在日本待了一年,回来之后,我就像突然“开了窍”,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在北京,我一边在“笑果文化”做线下脱口秀,一边继续创作我的民谣。
我曾是“笑果”线下脱口秀“噗哧”的北京区负责人。

我回国的第二天,就和史炎、ROCK、思文等人一起演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我也在北京、沈阳、杭州开过个唱,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少的时候二三十人。当自己的歌被人倾听,被人喜欢,是最开心的事。
对我来说,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在舞台上对着麦克风,弹着吉他,沉浸着一直唱到高音;或者当你讲完一个段子,观众们哄然大笑的时候。
当舞台上的我和台下的他们,都无比投入的时刻,一种特殊的共鸣就产生了,而这种共鸣能带给我无限能量。

2020年7月末,我在杭州和朋友一起成立了自己的脱口秀俱乐部“空手笑”。
白天写段子,晚上演出,生活谈不上规律,倒也算充实。
用手机备忘录记旋律的习惯还是没变,灵感乍现时,我会随手记下几句段子,或者一段音符。
如果人是一个核桃,那我的外壳是“喜剧人·胖达威”,而内核是“民谣魂·弓长紫”,它们都拥有我人性最深处的特质。
“弓长紫和胖达威”就是我的精神世界,无论是喜悦抑或悲壮,这都是我。

22
今年7月,我带着父亲一起去新疆旅行,这算是我们父子的第一次“正经出游”。
小时候,父亲带我去过不少地方,现在,该我带他出去转转了。
在喀什古城里乱逛的时候,我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块东西似曾相识,凑近一看,是一块破旧的地毯。

神奇的是,它的花纹和小时候我们家30年前摆的那一块地毯,一模一样。还记得我经常趴在上面看书、玩游戏,每次洗完澡都喜欢湿着脚上去踩……
三十年了,我至今清楚记得它的样子。
恍惚间,就像踏进了平行时空。我和父亲,坐在新疆古城的路边,一块如家般熟悉的地毯上。

后来,我又特意带父亲来到了“和田”。
父亲喜欢玉,在老家每每路过玉石摊子,他都要停下来看,没事儿还总和我显摆他手上带的那串玉石手链。
于是我带着他来到和田的一条河边,他兴致勃勃在河边低头寻摸了半天,想捞一块价值百万的玉石。

结果,一无所获。
他死心了,说:“河边也没有玉。和田都没有,再上哪里能有呢?”
一个多小时后,父亲找了几块类似于东北腌酸菜的大石头,宝贝似的准备带回沈阳……
只要他高兴,怎么都行。
旅行途中,我和父亲还是如十几年前一般“水火不容”,几句话就能怼起来,好几次差点动手,也许这就是我们父子俩的“相处之道”吧。
回到喀什的晚上,吃完饭也没啥事儿干,我和一个新疆小伙儿在民宿街边的沙发上,开始了新疆传统艺能:饭后茬琴。
他弹着都塔尔,唱了一首新疆民歌。我给他弹唱了我的原创:山神调。
唱到嗨的时候,他也一起拿着都塔尔给我伴奏,我们还热烈地讨论着汉族歌和维吾尔族歌各自的风格与局限性。
“你看维吾尔族的歌啊,通常就是这几个和弦,所以表达悲伤情绪的时候,不如汉族歌来得细腻……”我说。
他不服,又一首接着一首弹。
我们一起谈天,弹琴,喝酒,大笑。
无意中,我看到坐在旁边的父亲露出了笑容,他始终很安静,不说什么说话。
他的笑容,是那种自己孩子说些什么完全听不懂,但就感觉很高兴的笑容。

可能父亲根本没想到的是,我是因为他,因为他的那把老吉他,才走上音乐道路的。
我很确定,如果没有当年我砸坏他的那把吉他的负罪感,就不会有我现在的这些歌。
我们好像总是在互相亏欠,又不断弥补。
这么多年,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大概可以用赵本山的那句台词来形容:“凑活过呗,还能离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