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醸的面包
风过瑟鸣,漫弹人生;时光河畔,流水潺湲;炉围灶旁,我煮沉浮;原创到底,勤写广读;博客精神,佳文美图。

 不知道小时候面包对我是否有着终极的诱惑力,只知道有那么一次在电影院和爸妈一起看《德伯家德的苔丝》,片中出现的黄油面包镜头点燃了腹中饥肠的熊熊欲望,全然不顾周遭的其他观众,在电影院里大吵大闹要立刻吃面包,苔丝是谁,又遇了什么好人歹人,与之何干?一个小女孩,可以馋到为了讨一份零食就赖在地上不走,为了买条冰棍偷偷拿出存钱罐里的五分钱,为了喝不到的果汁一直臭着脸,这就是那时候的我。后来面包成为我童年的笑谈,它只是一个童年的符号。 不知道小时候面包对我是否有着终极的诱惑力,只知道有那么一次在电影院和爸妈一起看《德伯家德的苔丝》,片中出现的黄油面包镜头点燃了腹中饥肠的熊熊欲望,全然不顾周遭的其他观众,在电影院里大吵大闹要立刻吃面包,苔丝是谁,又遇了什么好人歹人,与之何干?一个小女孩,可以馋到为了讨一份零食就赖在地上不走,为了买条冰棍偷偷拿出存钱罐里的五分钱,为了喝不到的果汁一直臭着脸,这就是那时候的我。后来面包成为我童年的笑谈,它只是一个童年的符号。
 后来面包又成为另外一个俗套的符号,一个与爱情对峙的符号,在大多数人看来,面包与爱情是就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其实如果际遇足够好,面包与爱情是不会矛盾的。愈发现实的社会教会了无数女孩等待携带现成面包而来的人,并且还要细细考量面包的尺寸和材质。在一番又一番的权衡斟酌中爱情也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换物,放在天平上与面包一较轻重。 后来面包又成为另外一个俗套的符号,一个与爱情对峙的符号,在大多数人看来,面包与爱情是就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其实如果际遇足够好,面包与爱情是不会矛盾的。愈发现实的社会教会了无数女孩等待携带现成面包而来的人,并且还要细细考量面包的尺寸和材质。在一番又一番的权衡斟酌中爱情也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换物,放在天平上与面包一较轻重。

有那么一日我也落入了俗套的抉择,然而在那个相信“有情饮水饱”的季节里,逼我吃下一块面包兴许只会因噎废食难以下咽,倒不如喝着爱情的白开水,不加糖也清甜爽口。于是,面包再一次被我遗忘。再后来开始意识到饮水固然能饱腹,却终不能果腹,再多的水也只是饱腹的假像,然后片刻穿肠而过空空如也。终于在某个时体味了到没有面包的匮乏,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能十年数十年如一日的“有情饮水饱”并且不后悔自己曾经放弃的面包。我也许不是一辈子饮水也不饿的人,却也不是怀念曾经摆在手边面包的人,既然遇见了这个可以一齐饮水也作乐的人,也相信我们在一起也可以将水变成面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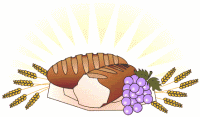
于是我们开始一起做面包,他带来了酵母和面粉,我有黄油糖盐,一起打造一个理想的面包,体验做面包的全过程快乐和艰辛并存。虽然面包还未进入烤箱,且只在发酵初期,单单闻着面包渐渐膨胀时散发出的香气,已有几分陶醉,等待面包的日子,怎么饥饿,都是有盼头的;只希望当面包烤好后,他掰开的暖暖软软的第一块若与我分享,这些日子的守候就没有枉然。
 在厨房做面包时会胡思乱想,从面包里参悟着人生,在面包的酵香中品味生活。收到这个面包机有两周的日子了,这是我们日子迈入小康或者小资的又一重大举措,我知道其实有不少勤劳巧手的主妇是用纯手工来和面做面包的,毕竟千百年来面包都是手揉出来的,只是现代人越来越懒,对机器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才催生了这些千奇百怪的发明。曾经很热衷于做蛋糕,买了无数个蛋糕烤模,却又嫌蛋糕热量太多束之高阁;面包是个折衷,特别是全麦面包,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它做早餐是不宜之举,所以告诫自己学习了一轮各式甜面包、面包圈、奶油面包等等后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最质朴的全麦面包。 在厨房做面包时会胡思乱想,从面包里参悟着人生,在面包的酵香中品味生活。收到这个面包机有两周的日子了,这是我们日子迈入小康或者小资的又一重大举措,我知道其实有不少勤劳巧手的主妇是用纯手工来和面做面包的,毕竟千百年来面包都是手揉出来的,只是现代人越来越懒,对机器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才催生了这些千奇百怪的发明。曾经很热衷于做蛋糕,买了无数个蛋糕烤模,却又嫌蛋糕热量太多束之高阁;面包是个折衷,特别是全麦面包,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它做早餐是不宜之举,所以告诫自己学习了一轮各式甜面包、面包圈、奶油面包等等后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最质朴的全麦面包。
 作为面包初学者,三分钟热度尚未消退,无论是和面、发酵、烘烤都意兴盎然。特别喜欢隔着透明机盖看白色的面团在面包机里有节奏有韵律变换着姿态和形状上下左右东摇西晃地舞蹈,面团就像一个牵了线的布偶,由一只invisible hand 牵动着旋转跌宕,生生把一团死面牵扯出千丝万缕的筋道,难怪著名的速成烘培食品公司Phillsbury 的吉祥物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白白小面人。发酵则更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面包机停止刹那,无论是拔掉电源还是任其在面包机的发面程序中继续发酵,那一点一点的膨大对面团是非常艰难又漫长的过程,那是用尽一生力气才能达成的圆满啊。这时候已经是满屋酵香。仿佛泡在啤酒的海洋里,终于明白为何啤酒又称为 “ 液态面包” 了。正当万事几近具备时,却要给面团当头一棒,挫掉刚刚集聚起来的所有锐气,取出放在案板上,分割成数个小块,很是袖珍,很难想象下一个轮回中它又能恢复到丰盈的体态。放任松弛十分钟后,开始包馅整形。 作为面包初学者,三分钟热度尚未消退,无论是和面、发酵、烘烤都意兴盎然。特别喜欢隔着透明机盖看白色的面团在面包机里有节奏有韵律变换着姿态和形状上下左右东摇西晃地舞蹈,面团就像一个牵了线的布偶,由一只invisible hand 牵动着旋转跌宕,生生把一团死面牵扯出千丝万缕的筋道,难怪著名的速成烘培食品公司Phillsbury 的吉祥物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白白小面人。发酵则更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面包机停止刹那,无论是拔掉电源还是任其在面包机的发面程序中继续发酵,那一点一点的膨大对面团是非常艰难又漫长的过程,那是用尽一生力气才能达成的圆满啊。这时候已经是满屋酵香。仿佛泡在啤酒的海洋里,终于明白为何啤酒又称为 “ 液态面包” 了。正当万事几近具备时,却要给面团当头一棒,挫掉刚刚集聚起来的所有锐气,取出放在案板上,分割成数个小块,很是袖珍,很难想象下一个轮回中它又能恢复到丰盈的体态。放任松弛十分钟后,开始包馅整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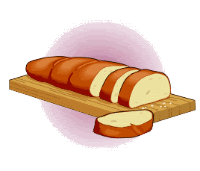 这一次尝试了做最为简单的圆面包,里面包上肉松,捏成浑圆状。烤箱里放一锅煮沸的开水,将包好的面团送入温润的烤箱做最后一次酝酿,其间难免不频频翕开烤箱门偷窥面团的动静,唯恐未达到梦想中的圆润。痴等一个小时后才能打开烤箱,拖出烤盘,蹲在烤箱外,匆忙却又得温柔地涂上蛋黄液,撒上白芝麻,任何延误和粗暴都会使好不容易涨大的面团瘪气,这面团怎么就这么不可思议地难伺候呢?实在应该好好讨教一番。一旦正式启动烘烤,这幸福的时光就只有十几分钟,只可惜我的烤箱没有上火,要期待靠下火来给面包上色美容真有几分困难,要达到增之一分则太焦,减之一分则太浅可不能掉以轻心,可即便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也只能烤出个差强人意的皮色,不过可以放心宣布第二次实践成功,尚需继续努力。捡出两个卖相最佳的准备送与他的同学,却总是错过时间,无法兑现,只等下次再做新鲜面包时与人分享了,不过我做的新出炉的热面包,第一口定要由他亲阅,谁叫他是幸福的银筷子呢? 这一次尝试了做最为简单的圆面包,里面包上肉松,捏成浑圆状。烤箱里放一锅煮沸的开水,将包好的面团送入温润的烤箱做最后一次酝酿,其间难免不频频翕开烤箱门偷窥面团的动静,唯恐未达到梦想中的圆润。痴等一个小时后才能打开烤箱,拖出烤盘,蹲在烤箱外,匆忙却又得温柔地涂上蛋黄液,撒上白芝麻,任何延误和粗暴都会使好不容易涨大的面团瘪气,这面团怎么就这么不可思议地难伺候呢?实在应该好好讨教一番。一旦正式启动烘烤,这幸福的时光就只有十几分钟,只可惜我的烤箱没有上火,要期待靠下火来给面包上色美容真有几分困难,要达到增之一分则太焦,减之一分则太浅可不能掉以轻心,可即便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也只能烤出个差强人意的皮色,不过可以放心宣布第二次实践成功,尚需继续努力。捡出两个卖相最佳的准备送与他的同学,却总是错过时间,无法兑现,只等下次再做新鲜面包时与人分享了,不过我做的新出炉的热面包,第一口定要由他亲阅,谁叫他是幸福的银筷子呢?








/> | />
秋瑟潺湲 发表评论于
回复毛毛-妈的评论:
其实只是“馒头包子”式的面包
Littletreeat 发表评论于
面包好诱人啊~~~
mm果然是智慧的女人呢,面包与爱情的比喻很贴切哦
心知语 发表评论于
看了很感动,我也有同感。老公永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等待他满意的点头然后是我幸福的笑容。
毛毛-妈 发表评论于
面包烤的好棒哦。
whateverj 发表评论于
写的不错,面包看起来更好!

 不知道小时候面包对我是否有着终极的诱惑力,只知道有那么一次在电影院和爸妈一起看《德伯家德的苔丝》,片中出现的黄油面包镜头点燃了腹中饥肠的熊熊欲望,全然不顾周遭的其他观众,在电影院里大吵大闹要立刻吃面包,苔丝是谁,又遇了什么好人歹人,与之何干?一个小女孩,可以馋到为了讨一份零食就赖在地上不走,为了买条冰棍偷偷拿出存钱罐里的五分钱,为了喝不到的果汁一直臭着脸,这就是那时候的我。后来面包成为我童年的笑谈,它只是一个童年的符号。
不知道小时候面包对我是否有着终极的诱惑力,只知道有那么一次在电影院和爸妈一起看《德伯家德的苔丝》,片中出现的黄油面包镜头点燃了腹中饥肠的熊熊欲望,全然不顾周遭的其他观众,在电影院里大吵大闹要立刻吃面包,苔丝是谁,又遇了什么好人歹人,与之何干?一个小女孩,可以馋到为了讨一份零食就赖在地上不走,为了买条冰棍偷偷拿出存钱罐里的五分钱,为了喝不到的果汁一直臭着脸,这就是那时候的我。后来面包成为我童年的笑谈,它只是一个童年的符号。 后来面包又成为另外一个俗套的符号,一个与爱情对峙的符号,在大多数人看来,面包与爱情是就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其实如果际遇足够好,面包与爱情是不会矛盾的。愈发现实的社会教会了无数女孩等待携带现成面包而来的人,并且还要细细考量面包的尺寸和材质。在一番又一番的权衡斟酌中爱情也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换物,放在天平上与面包一较轻重。
后来面包又成为另外一个俗套的符号,一个与爱情对峙的符号,在大多数人看来,面包与爱情是就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其实如果际遇足够好,面包与爱情是不会矛盾的。愈发现实的社会教会了无数女孩等待携带现成面包而来的人,并且还要细细考量面包的尺寸和材质。在一番又一番的权衡斟酌中爱情也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交换物,放在天平上与面包一较轻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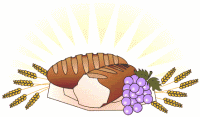
 在厨房做面包时会胡思乱想,从面包里参悟着人生,在面包的酵香中品味生活。收到这个面包机有两周的日子了,这是我们日子迈入小康或者小资的又一重大举措,我知道其实有不少勤劳巧手的主妇是用纯手工来和面做面包的,毕竟千百年来面包都是手揉出来的,只是现代人越来越懒,对机器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才催生了这些千奇百怪的发明。曾经很热衷于做蛋糕,买了无数个蛋糕烤模,却又嫌蛋糕热量太多束之高阁;面包是个折衷,特别是全麦面包,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它做早餐是不宜之举,所以告诫自己学习了一轮各式甜面包、面包圈、奶油面包等等后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最质朴的全麦面包。
在厨房做面包时会胡思乱想,从面包里参悟着人生,在面包的酵香中品味生活。收到这个面包机有两周的日子了,这是我们日子迈入小康或者小资的又一重大举措,我知道其实有不少勤劳巧手的主妇是用纯手工来和面做面包的,毕竟千百年来面包都是手揉出来的,只是现代人越来越懒,对机器的依赖度越来越高才催生了这些千奇百怪的发明。曾经很热衷于做蛋糕,买了无数个蛋糕烤模,却又嫌蛋糕热量太多束之高阁;面包是个折衷,特别是全麦面包,几乎没有理由认为它做早餐是不宜之举,所以告诫自己学习了一轮各式甜面包、面包圈、奶油面包等等后还是要回归到最原始最质朴的全麦面包。 作为面包初学者,三分钟热度尚未消退,无论是和面、发酵、烘烤都意兴盎然。特别喜欢隔着透明机盖看白色的面团在面包机里有节奏有韵律变换着姿态和形状上下左右东摇西晃地舞蹈,面团就像一个牵了线的布偶,由一只invisible hand 牵动着旋转跌宕,生生把一团死面牵扯出千丝万缕的筋道,难怪著名的速成烘培食品公司Phillsbury 的吉祥物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白白小面人。发酵则更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面包机停止刹那,无论是拔掉电源还是任其在面包机的发面程序中继续发酵,那一点一点的膨大对面团是非常艰难又漫长的过程,那是用尽一生力气才能达成的圆满啊。这时候已经是满屋酵香。仿佛泡在啤酒的海洋里,终于明白为何啤酒又称为 “ 液态面包” 了。正当万事几近具备时,却要给面团当头一棒,挫掉刚刚集聚起来的所有锐气,取出放在案板上,分割成数个小块,很是袖珍,很难想象下一个轮回中它又能恢复到丰盈的体态。放任松弛十分钟后,开始包馅整形。
作为面包初学者,三分钟热度尚未消退,无论是和面、发酵、烘烤都意兴盎然。特别喜欢隔着透明机盖看白色的面团在面包机里有节奏有韵律变换着姿态和形状上下左右东摇西晃地舞蹈,面团就像一个牵了线的布偶,由一只invisible hand 牵动着旋转跌宕,生生把一团死面牵扯出千丝万缕的筋道,难怪著名的速成烘培食品公司Phillsbury 的吉祥物就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白白小面人。发酵则更是一个奇妙的过程,当面包机停止刹那,无论是拔掉电源还是任其在面包机的发面程序中继续发酵,那一点一点的膨大对面团是非常艰难又漫长的过程,那是用尽一生力气才能达成的圆满啊。这时候已经是满屋酵香。仿佛泡在啤酒的海洋里,终于明白为何啤酒又称为 “ 液态面包” 了。正当万事几近具备时,却要给面团当头一棒,挫掉刚刚集聚起来的所有锐气,取出放在案板上,分割成数个小块,很是袖珍,很难想象下一个轮回中它又能恢复到丰盈的体态。放任松弛十分钟后,开始包馅整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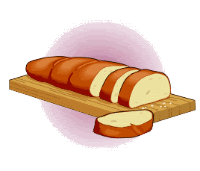 这一次尝试了做最为简单的圆面包,里面包上肉松,捏成浑圆状。烤箱里放一锅煮沸的开水,将包好的面团送入温润的烤箱做最后一次酝酿,其间难免不频频翕开烤箱门偷窥面团的动静,唯恐未达到梦想中的圆润。痴等一个小时后才能打开烤箱,拖出烤盘,蹲在烤箱外,匆忙却又得温柔地涂上蛋黄液,撒上白芝麻,任何延误和粗暴都会使好不容易涨大的面团瘪气,这面团怎么就这么不可思议地难伺候呢?实在应该好好讨教一番。一旦正式启动烘烤,这幸福的时光就只有十几分钟,只可惜我的烤箱没有上火,要期待靠下火来给面包上色美容真有几分困难,要达到增之一分则太焦,减之一分则太浅可不能掉以轻心,可即便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也只能烤出个差强人意的皮色,不过可以放心宣布第二次实践成功,尚需继续努力。捡出两个卖相最佳的准备送与他的同学,却总是错过时间,无法兑现,只等下次再做新鲜面包时与人分享了,不过我做的新出炉的热面包,第一口定要由他亲阅,谁叫他是幸福的银筷子呢?
这一次尝试了做最为简单的圆面包,里面包上肉松,捏成浑圆状。烤箱里放一锅煮沸的开水,将包好的面团送入温润的烤箱做最后一次酝酿,其间难免不频频翕开烤箱门偷窥面团的动静,唯恐未达到梦想中的圆润。痴等一个小时后才能打开烤箱,拖出烤盘,蹲在烤箱外,匆忙却又得温柔地涂上蛋黄液,撒上白芝麻,任何延误和粗暴都会使好不容易涨大的面团瘪气,这面团怎么就这么不可思议地难伺候呢?实在应该好好讨教一番。一旦正式启动烘烤,这幸福的时光就只有十几分钟,只可惜我的烤箱没有上火,要期待靠下火来给面包上色美容真有几分困难,要达到增之一分则太焦,减之一分则太浅可不能掉以轻心,可即便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也只能烤出个差强人意的皮色,不过可以放心宣布第二次实践成功,尚需继续努力。捡出两个卖相最佳的准备送与他的同学,却总是错过时间,无法兑现,只等下次再做新鲜面包时与人分享了,不过我做的新出炉的热面包,第一口定要由他亲阅,谁叫他是幸福的银筷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