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照乡村文革的一面魔镜
——读老村的《骚土》
(瑞典)茉莉
举起一面平常的镜子映照世界,那不是有才华的作家所为,因为文学本来就是对抗简单化的艺术。但陕西籍作家老村(蔡通海)手里拿的镜子,如同西汉千年魔镜,具有幻术般的投影透视力。在这面特殊魔镜的映照之下,我们可以窥见半个世纪前中国乡村文革那那一幅已深深隐没的黑暗图景。
泰戈尔曾说:“历史慢慢地闷死了它的真实,但又在痛苦的可怕忏悔中匆匆地拼命去复活它。”老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他从被扭曲的历史中探寻到埋藏于大地深处的真实,以卓尔不群的独立精神与洞察力,践行了一次被中国官方文学讳莫如深的叙述。
在小说《骚土》中,老村以真实和富有同情心的书写,在芜杂荒诞的中国乡村历史里,编织出精彩的人物、事件与场景,让读者从世态民情中穿透历史和人性,认识“权力怎样损害着乡村这一恒久命题”(吴洪森语)。这部小说蕴含深沉的智慧、义无反顾的激情与犀利的反讽,冲击着历史社会的表层和本质,展示出一个时代的痼疾与病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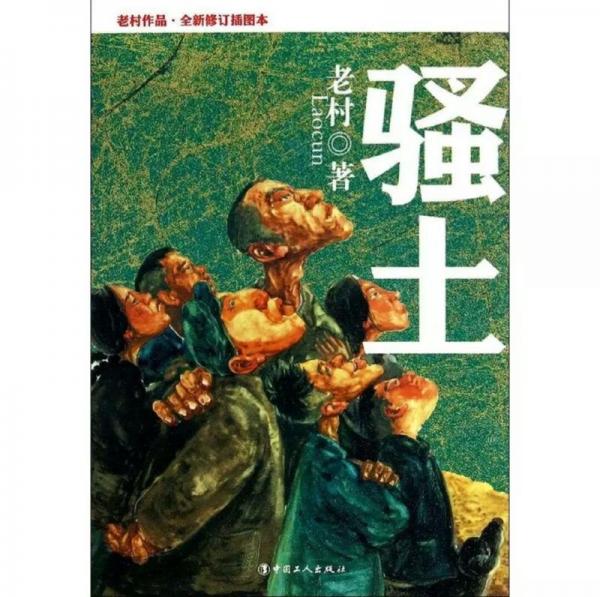
@ 索尔仁尼琴要求“主要的真实”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文革主要是给城镇带来严重危害,对乡村的影响不是很大。然而老村这个从陕西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讲述了一个叫鄢崮村的村子怎样陷入文革的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在那种状态下,是比做奴隶还要恐怖的一件事情。”
当年是家里最小的男孩,老村从小就和父母睡在一面土炕上。在深长的黑夜里听父母谈话,令他终生难忘的,是父母亲每个晚上那一声长长的叹息:“明天的日子该怎么过啊?”贫困的家境在男孩心中留下沉重的阴影,更让童年老村惊心动魄的是,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因饥饿而打劫粮库的农民被枪毙的过程。
当这个男孩长大进入都市后,中国大地一场又一场的劫难制造了众多的冤魂,原置于记忆角落的文革伤痛由此被不断唤醒。他孤单而决绝地返过身去,拾起自己的童年乡村回忆,为凋零破败的故土与父老乡亲写作。
这对老村来说绝不是一件浪漫轻松的事情。自1983年始,他一贯的文学主题是:饥饿和虐待、专制和反抗。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这本被评论家认为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极品”的小说《骚土》。从最初的删节版到最终的足本出版,又用了近20年,其艰辛磨砺可见一斑。

奥威尔曾在《文学的阻碍》一文中谈到文学与极权的关系。他认为极权制度会造就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它既不会容许作家忠实地记载事实,也不会容许作者如实反映感情,而这两者都是文学创作必须的元素。就当今中国文学的现状来看,在极权压制下的文学,逐渐造成快餐化、泡沫化、空心化的效果,成为无聊的梦呓和彩色的文字游戏。
极权下文学的病因,就如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那么,索氏所说的“主要的真实”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文学可以有各方面的真实,可以有个人的呢喃之语,但“主要的真实”,必须是因应复杂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必须是有重量的,只有绝望的黑暗中,往道德良知的土壤下深入探索的作家才能找到。
而老村就是当今中国极为稀少的直面“主要的真实”的作家。他自我勉励说:“总得要有人做些精致的东西。”在笔者看来,老村所要做的“精致的东西”,除了别有韵味特色的语言和高超的写作技巧之外,更涉及对历史现实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即将底层的真实还原出来,将罪人以文学方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在中国至今没有结束,因此,老村的这本奇异的小说,仍然是现实的写照,是当代中国真正的文学呼吸。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所定义的:“每一种写作,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人们需要这种写作,来清理、解释自己所处的吊诡无序的世界。
@ 乡村文明遭“寇盗式的破坏”
《骚土》一开头,文革伊始,瘸腿的季工作组进驻鄢崮村。此时乡村千百年来的稳定结构已被摧毁,村民们已有过天翻地覆的阅历,经历了诸如国共内战、土改斗地主、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大饥荒等动荡与磨难,应该见怪不怪了。然而,季工作组的到来,仍然在闭塞麻木的乡村引发了一场无事生非的喧闹与畸变。
这个时常做梦被毛泽东接见的政治怪物,满脑子“阶级斗争”的季工作组,仿佛是一架永不停息的政治发动机。那土地早已充公、阶级差别已消失的西北乡村,在他的折腾之下,平地冒出一场又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来。
一种若隐若现的沉重感,就从这荒诞调侃的描绘之中显露出来。小说叙述的人物和故事,让我们看到,极权在偏僻乡村如何肆无忌惮,而人民又怎样被迫地成为极权横行的土壤。在鄢崮村,口口声声毛语录的季工作组就是中共和毛的化身,在他面前,乡村干部一个个奴颜婢膝,村民们一个个点头哈腰。
在老村深具反讽的笔调下,乡民们不论聪慧狡黠,还是愚钝呆傻,都具有千年专制下农民散沙般的特点,如原子化的个体。在被集体化剥夺了土地之后,不知政治权利为何物的乡民,连自己的利益和方向也搞不清楚。他们浑浑噩噩地跟着季工作组的指挥棒转,民众和权力建立起一种人身依附的关系。即使处在狂热的革命时代,乡民们也不能不如蝼蚁一般,卑贱无助且辛劳地活着。
当时混乱的乡村文革也和城镇一样,首先拿读书人来开刀,小学校的教书匠杨文彰第一个被抓出来批斗,学校停课闹革命。而后,乡村在革命的名义下癫狂起来,欺骗和谎言伤害人们的心灵。动荡的时局给人性之恶展示机会,人们的私怨和宿仇开始发酵。此时,个体的行为就不再由他们自己的人格来决定,而被来自外界的权力意志所决定。
作家极尽揶揄讽刺之能事,以漫画般的手法描绘出的一场场的荒诞闹剧,展现出鄢崮村热热闹闹的众生相,且穿插着类似于三言两拍的乡野情色故事。中国西部农民的苦难、愚昧和麻木被描写得栩栩如生。读者因此看到,在传统伦理被革命瓦解的乡村,缺乏自我权利意识的无知乡民,是如何轻易地被极权所煽动利用,成为暴政的基础。文革这场规模巨大的瞎折腾,对残余的乡村文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都造成如鲁迅所说的“寇盗式的破坏”。
“毛泽东”这个名字在小说中贯穿始终。当季工作组进入鄢崮村,毛泽东便给他托梦。在奸淫了房东福堂婆娘后,季工作组又以背诵毛泽东诗词做掩盖。村痞庞二臭强奸少女时,也是带着闪闪发光的毛泽东像章,且以像章作为交换条件。每一次对村人实施的迫害,掌权者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进行。以毛泽东无所不在的描写,作者告诉读者,所谓《骚土》之骚的真实秘密是:毛泽东强暴了他的人民。
@ 阿Q之后最优秀的文学典型
所有的优秀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挑衅性的问题。在《骚土》中,老村对时代的质问,是通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提出来的。在该书众多人物中,有两位典型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最令人震撼,都让人看到:社会的演变如何深深改变个体的存在,如何导致生命的连续性与一致性的断裂。
一位是邓连山,鄢崮村的地主。这个人物与《白鹿原》里的地主白嘉轩有相似之处:都是凭借勤劳和智慧积累了土地财富,是乡村中救助贫困、守护乡邻的忠厚仁义之士。但邓连山很倒霉地碰上了土改,作为地主被清算,家中金银财产被连锅端,还因为在猪圈里发现手榴弹,被以“阴谋反攻倒算”罪名给判了十年牢狱。同是在民国承担传统道德责任的乡绅,邓连山却不如白嘉轩那样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他似乎更像一个纯粹的地主,经历巨大的厄运后,他原有的自我信念和道德原则荡然无存。
在老村的故事里,当年邓连山曾是“虎虎势势的一条大汉”,为人敦厚,极讲诚信。在莲花寺监狱劳改后,他变成了“三勤”积极分子:一是汇报思想勤;二是请示工作勤;三是学习《毛选》勤”。就如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瑞典人质,爱上了抢劫自己的绑匪,邓连山成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阿Q曾经被赵老爷抽了一个嘴巴,说他“不配姓赵”,他没法反抗。而邓连山在狱中不但没有反抗,反而被彻底驯化。他勤读毛选改造思想,其奴性深入骨髓。一次,邓连山遭大队民兵的暴打,他居然还嫌人家下手不狠。在完全丧失自我尊严之后,邓连山还接受了红朝灌输的“阶级仇恨”意识,为了他所爱戴的领袖,他竟然告黑状出卖自己的乡邻,导致带领村民开仓偷粮的郭大害被枪毙。在小说的结尾,邓连山终于良心觉醒,自缢在村东的柿树上。
可以说,邓连山是中国文学史上继阿Q之后塑造得最成功的文学典型。老村既写出了这个人物鲜明的个性特点,又通过他那令人吃惊的人格变化,反映出文革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描述人们在丧失尊严感之后的变态心理,具有相当的共性与普遍性。凡是经历过文革的读者都知道,当年如邓连山一样因自我改造思想而丧失良知的人,为向共产党表忠心告密陷害他人的人,几乎遍及中国城镇乡村,甚至包括大城市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但很少有人像邓连山一样为之自杀赎罪。
@ 为乡村最后的好汉唱一曲挽歌
中国乡村社会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道德,如善、孝、礼、勤等价值观,在由中共所率领的农村地痞及乌合之众手里,短短十几年时间,就被以摧枯拉朽之势给摧毁了。但老村并没有将历史一笔简化,而是以“呕出几升血来”的辛苦,思考那场浩劫中的乡村之演变以及人的全部复杂性:那里有奴役、有驯化、也有不屈的反抗。
忠实于生活的小说家,总是以塑造光彩熠熠的人物为旨归。《骚土》中另一个人物典型,是具有悲剧英雄气质的青年郭大害,老村视此人物为“黄土地上的真人”,将他的死亡视为中国农业社会梁山好汉式的英雄主义的终结。
老村娓娓道来,叙述了郭大害在矿山出事故后回村调养的故事。这个年轻人好善乐施救助乡亲,他在灯下痴心读《水浒》,并与村中十三男儿结义为兄弟,一起舞枪弄棒。郭大害与哑女之间的纯真美好的情意,是这本小说最温暖人心的章节。
在小说后半部分,郭大害带领村民开仓分粮之事件,无疑是这部文革小说的高潮所在。当时季工作组离村,几个基层干部勾结,偷偷私分集体小麦。气红了眼的村人找郭大害寻求主张,大害便想出一个“智取生辰纲”的主意,打个“借条”就撬开粮仓,让各家分粮救济饥荒。这样,一群热血青年即刻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大害本人被押到高崖下枪毙。
这位梁山好汉式的乡间英雄,不是老村凭空虚构出来的。如前所述,老村童年时目睹了一个因打劫集体粮库的农民被枪毙事件。中国自五十年代末的大饥荒到文革,因饥饿活不下去,农民的抢粮事件时有发生。例如四川汉子李文忠就曾持枪抢库开仓济民,自己因此被判重刑。
为在文革中反抗极权的乡村青年,老村洒下了一掬同情泪。但老村书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既热情赞赏郭大害的勇敢仗义,也冷峻地看到他的局限性,认识到郭大害的农民性格有“阿Q式的厚道和狡黠”,此外还有“贾宝玉式的的乖张和良善”。在统治者拥兵自重的当代,这类年轻人所谓传统的“水浒”好汉式的反抗,注定逃不脱失败的命运。
一部《骚土》,是老村为在文革遭难的乡村吟唱的一曲无奈而悲凉的挽歌,其中暗藏的是一把打开中国以及中共政治秘密的钥匙,中共文学当局因此对此书三缄其口。尽管思想内容深沉凝重,但善于揶揄戏谑、有插科打诨的说书才华的老村,是绝不会让自己的小说沉闷无趣的。他用通俗的喜剧手段写悲剧,语言鲜活生动,雅俗共赏。这部奇特的小说有着深远绵长的魅力,正如老村自己所期待的:“给备受劳苦的大众带去娱乐,带去对历史沉沉的正视。”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