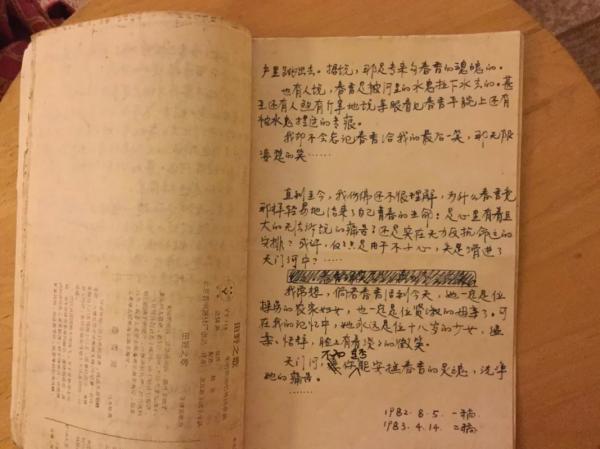|
百度图片----70年代的天门河 百度介绍:
当年的知青照 逝去的岁月有如流水,循着流水,总会找到它曾滞留过的港湾。我生命的河流,曾随着那一度势不可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滚滚浪潮,被卷入江汉平原上一个秀丽的小村庄,在那里度过了我青春岁月中最富于幻想的那段时光。 天门,很好听的名字----通往天堂之门!这是一个充满神奇幻想的名字,每当我想到天门,我总会想到那条环绕着小村庄的天门河,还有一个名叫春香的姑娘。 (1) 第一次看见春香,就是在天门河边。天门河那时还是清澈透明的,河水蜿蜒曲折地流过村庄,村子名叫沙口,行政所属刘集公社,全称天门县卢市区刘集公社沙口大队,我们4个人分在第一小队。 那是我们刚到的第一天,一条渡轮把我们4人连同我们的行李都卸在天门河岸,我们站在河边等着队长来给我们分配住处,行李散放在脚边。村里的小孩子满村跑,用天门话大声喊:来了四个“青年知识”,一个男的,三个“坛子”!后来我们才晓得,天门话里“坛子”就是没有出嫁的女孩。 他们对我们的行李也评头论足,一个小男孩惊奇的说:看!他们还带了箱子!另一个看上去非常有见地的年青人说:当然要带箱子,他们是来扎根的!说话的年青人挑着满满一担水,扁担颤颤悠悠在他的肩头晃动,那个年青人叫五金,我们混熟了以后都喊他“五金哥”,他是村里的百事通。 于是又有人发问:扎根?么事是扎根?五金哥权威地总结说:扎根就是一辈子都在这里,不走哒!说完以后他就挑着水走了,他身后的人群啧啧有声,不知是赞叹还是惋惜。这时我看见人群中有个脸盘黝黑的姑娘微微一笑。 河上突然来了一阵喧哗,原来有两条用红绸子扎在一起的木船划过来了,船上有人吹唢呐,有个穿红色衣服的女孩在大声哭,哭得惊天动地的感觉,边哭边念念有词,现在想起来很像美国的“说歌”。木船上装满了箱子柜子木桶之类的家具,吹唢呐的人看见大家都在围观,吹得越发起劲。 我们冒冒失失问旁边看热闹的是不是有人家里死了人?马上遭来大家一致的白眼,有个人还谴责地说:鬼扯打胡说,这是送亲的船,人家是在嫁姑娘哒!这时我看见那个黑黑脸盘的姑娘又咬着嘴唇笑了。 姑娘们在那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四口箱子,两台柜子!”“脚盆油的好亮!”“这姑娘伢哭的真好听!”我不禁愕然,在我的词典里,“哭”和“好听”是断然搭配不到一起的。 后来我才晓得,天门这一带的人(应该还包括沔阳潜江洪湖),嫁姑娘是十分讲究出嫁前的一场哭的,不但要放声大哭,还要边哭边说,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把自己的家史成长史还有对亲人的依恋不舍在哭声中娓娓而谈细细道来。家里有女儿的人家,女儿还小的时候,母亲就会带着女儿去观摩人家嫁姑娘,听听人家怎么哭,“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样日后自己出嫁的时候才会哭出精彩哭得好听,才能获得乡亲们的好评。 看热闹的人群散去了,那女孩还在河边发呆。直到有人大喊一声“春香,该走哒!”,这才仿佛惊醒了梦中人,她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跟同伴们一起走了。原来这姑娘名叫“春香”,乡土气味很浓,古装戏里演丫环的好像也都是叫这个名字。我记住“春香”这个名字的同时也记住了她的笑脸。 (2) 下放的知青都有国家发的安家费,队里用这笔钱给我们盖了房子。房子盖在堤上,紧靠着天门河。来河边洗衣服挑水的人都爱来我们屋里,他们对我们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东看看西瞄瞄,还会跑到灶台边掀开锅盖看看我们吃什么。 春香也常来,她总是站在大门口靠着门框,笑眯眯地看我们忙忙碌碌,好像看着我们做饭是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做饭时常常手忙脚乱,从来都没配合好--不是烧灶的火没烧起来满屋都是浓烟,就是锅里的油已经烧的青烟直冒而菜还没切好。我们的饭总是夹生的,菜不是盐放得太多,就是放得太少。有时饭还没做好队长就在外面高喊:出工了!我们只有慌慌张张扒几口饭,撂下饭碗就夺门而出。 我们吃的菜是队里按人头不定期分的,当地人都会做腌菜,留着青黄不接的时候吃。我们每次分了菜就敞开了吃,没有菜的时候我们就吃酱油拌饭,有时酱油也没有了我们只能吃白饭。有天我们正吃饭,春香来了,手上端着一碗腌菜。她把腌菜放在我们桌上说:“好几天都没见你们吃菜了,这碗腌菜你们可以将就吃几天,队里过几天就要分菜了。” 春香拿了一块砖头在我们的饭桌旁坐下看我们吃饭,看得津津有味。过了一会她问我们:“听说你们城里人炒菜要放酱油,把菜染黑了再吃,是不是真的?” 我们笑起来,说不是把菜染黑,酱油是用来调味道的。她恍然大悟地说:“你们青年知识来了以后,供销社的酱油卖得快多了,原来放在那里一两年都没人买,我以后也要去买一瓶,看看放了酱油的菜是不是比不放要好吃。” 春香逐渐和我们熟悉了,成了我们的常客,她比我们大一岁多,我们喊她“春香姐”。她虽然皮肤比较黑,但是黑的很有味道,她特别喜欢笑,笑起来一排珍珠贝般的牙齿闪着光泽,细细长长的一双眼睛波光流转,格外温柔妩媚。背地里,我们喊她“黑郁金香”,那是法国作家大仲马一部小说的名字,我们把这个好听的名字送给了她。
当年的知青屋 (3) 我们下放的那个村子叫沙口,村里有大约40几户人家,姓刘的居多,而且都是本家人,大家沾着亲带着故,在村子里很有势力。春香家是外姓人,但她父母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惹是生非,在村里人缘极好,她父亲可能有一点文化,是队里的技术员。春香是老大,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春香在家里是个娇娇女,父母很宠爱她。大概受父母的影响,春香的话也很少,脾气随和,她从不大声说话,更不会跟人争执,总是微微笑着。 “栽秧割麦两头忙,哪有闲空回娘家“,这是湖北著名的民歌演员蒋桂英的一首天门民歌《回娘家》里的一句歌词(蒋桂英是天门蒋场人,蒋场距离我们下放的沙口村大约有8里地)。我们下放不久就赶上了农村中最忙的季节。 那是5月末,天气已经开始热了,麦子成熟要割上来,不然下雨就会烂在地里,晚稻也要抢季节插下去,过了季节长出来的就不是稻谷而是稻草了。我们天天要去离村子很远的水田插秧,插秧的人都自带午饭,春香还要带一罐清水,但她自己从来不喝,总是让给我们喝,她自己则从水洼子里或者水塘边捧一点水喝。“你们城里人金贵,我们么事水都可以喝”,她总是笑着这样说。 在水田里栽秧的时候,春香也总是跟我们站在一排,她是干农活的好手,在秧田里,只见她两只手上下飞舞,一边栽一边往后退,仿佛变魔术般,她的前面很快就变出一排绿油油的稻田来。她栽完自己的一垄田,就会过来帮我们栽,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歇口气了。 有天我们栽完一块田,爬到田埂上靠着一棵大树乘凉。春香突然问:“你们城里的房子都蛮高,是吧?” 春香告诉过我们,她长这么大从没出过远门,她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蒋场,她老爸划船带她去赶集,还在那里扯了几尺花布。回来后她高兴地把花布拿给我们看,“这是在那里的商店里买的!”她特别强调“商店”这两个字,显得非常自豪。 离我们村几里地外的净潭有一个小供销社,只卖油盐酱醋糖肥皂等,村里人要买日用杂货才会走去那里。平日里他们穿衣都是自己织布,鞋也是自己做。“商店”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奢侈品,而“逛商店”则是享受奢侈品的过程,村里只要哪个姑娘去过一次商店,那就是村里的重大新闻,她们会津津乐道十天半个月仍然意犹未尽。 城市对于春香来说,大概就像天国一样遥远陌生神奇,她那简单幼稚到近乎贫乏的头脑里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的。 我们无法对春香形容出城市的模样,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才会懂得“城市”是什么。“城市”不是一样具体东西,可以形容它的形状,颜色或者味道,“城市”是一个地理概念。我们告诉她说城里的房子确实很高,武汉是个大城市,大城市的房子就更高了。 “那…..到底有几高涅?”春香四下里张望,想找到一个参照物,周围实在没什么可参照对比的,于是她指着我们靠着的树问:“有这棵树高吗?” 我们说:“城里的房子比这棵树要高多了!” 春香惊讶地说:“真的?那不是看不到房顶吗?” 我说:“你把头仰起来就看到了呀!” 春香困惑地说:“啊呀,那戴的斗笠都会掉下来涅!” 我们大笑起来,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人仰马翻,我正在喝水,一口水差点喷出来喷到春香的身上。 春香脸红地低下头,没有再提问。等我们终于止住了笑,才发现春香已经一个人下田去栽秧了,整整一天她都没跟我们说话。 我这才明白,我们深深地伤害了春香的自尊心。我们那么肆无忌惮地嘲笑她,是的,她很无知,她不知道什么是城市,可那并不是她的过失,我们有什么资格取笑她? 收工时,我站在田埂上等她,她总是最后一个从田里上来。我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想对她表示友好,她仍然不出声,两眼紧盯着脚下的泥地。 我突然没头没脑地对春香说:“春香姐,你以后跟我们一起回武汉吧,我带你到城里去玩,你可以住在我们家里!” 她抬头望着我,眼睛里充满怀疑:“真的?我怎么去得了呢?而且我那么笨!” 我着急地摇着春香的肩膀:“去得了的,去得了的!”好像是我们明天就要动身一样。 我接着又补充了一句:“春香姐,你一点也不笨,我们再也不笑你了,我向毛主席保证!” 我们两个人突然都忘乎所以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暮色苍茫的田野里飘得很远,很远…… (4) 秧栽完了,麦也割上来,就入夏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田里的活主要是锄棉花草,这是村里姑娘们喜欢的时光----不用下水田,活也不重,这时候她们会尽可能把自己最好的衣服穿出来。农村姑娘的爱美天性有时比城里女孩子还要强烈,她们绝不放过任何展示自己的机会。 一天,我在天门河边洗衣服,一边洗一边放声高唱。“洪湖水浪打浪”唱完了接着唱“红岩上红梅开”,唱着唱着我觉得身后有人,回头一看是春香,她也端着一盆衣服,看来已经站在那里有好一会了。 “你唱的真好听,跟戏匣子里一样!”她由衷地赞叹。 我告诉她,读小学的时候,我是武汉市少年儿童合唱团成员,经常参加各种演出,在可以容纳千把人的会场独唱领唱从来都不会怯场,我还在她说的“戏匣子”,也就是广播电台唱过歌,并且上过电视节目(她根本不晓得什么是电视),她惊讶得嘴都微微张开了。 “我们村的环元和桃枝也去区里唱过花鼓戏的!”春香崇拜地说。 “你会唱花鼓戏吗?”我问春香。天门的女孩,差不多个个都会唱花鼓戏,那是她们的童子功。我们刚去的时候,就有贫下中农告诉我们说,饥荒年家家户户外出逃荒,女伢们要是不会唱花鼓戏是讨不到饭的。 春香有点害羞地说:“我唱得不好。”但是她还是小声唱了一段《红灯记》里铁梅的唱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是用花鼓戏的唱法翻唱的。她唱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河水。 “你唱的蛮好,”我夸奖她说,“而且《红灯记》用花鼓戏唱也蛮好听。” 春香脸红了,“我比桃枝她们唱得差多了。她们要是唱会更好听。”看得出来,我的夸奖使春香非常高兴。 我们洗完衣服,我牵了一根绳子晾晒,春香也跟我帮忙。 “你们怎么都是破衣服涅?”春香问我,她手里拿着一件衣服正在往绳子上搭。 我扫了一眼我们正在晾晒的衣服,的确,我们的衣服上面几乎都是有补丁的,尤其是我的一条长裤,是我哥哥的,上面前前后后有四块大补丁,而且还是男式裤子,前面开门的那种,在那个年代真没有女生会穿这样的裤子。
“你们瞧不起我们乡下,连好衣服都不肯带来。”春香有些伤心地说。 我不晓得怎么跟她解释,我们确实没带一件像样的衣服。在棉田里,姑娘们像一群彩色的花蝴蝶,而我们几个永远穿着洗的发白的蓝布裤,有补丁的灰衬衫,好像三只灰溜溜的地鼠。 我注意到春香穿着一件湖蓝色的绸裤子,裤腿宽宽的,粉红色的盘扣斜襟绸衫,腰身细细的,微风吹来,给人飘飘欲仙的感觉。 “春香姐,你的衣服真好看!”我赶紧把话题岔开。 春香笑了:“我长得黑,穿么衣服都不好看,要是你们穿会更好看的。”让她开心真的很容易。
05年重回天门,天门河水已经浑浊不堪了,我们身后站着的就是五金哥。 (5) 天门一带的农村,有从小订亲的习俗,我们村里的姑娘也几乎都订了亲。农村的女孩是早熟的,到了十六七岁就开始悄悄为自己准备嫁妆了。订了亲的女孩子,男方逢年过节就要给女方送茶礼。茶礼的内容很丰富,一般包括烟酒茶叶糕点,腌鱼腊肉活鸡活鸭以及给未来的岳父母和未婚妻买的布料等等。当然送茶礼还要看家庭环境以及经济承受能力,富裕的家庭茶礼送得大气,现在的流行语言是“高大上”,而家境贫寒送的茶礼就很一般。但无论如何男方都要送,一直送到姑娘出嫁,媳妇娶进门。 由于订亲订得早,男方要送十几年的茶礼,所有重大的节日都要送,每年送三到四次。这样的订亲虽然没有正式的契约,但双方都是极守信用的,一旦订了亲就不容翻悔,最后的嫁姑娘只不过是走一个过场,因为姑娘早就是男方的人了。“嫁姑娘”很有点像现在的“走秀”,男方就是将自己的新娘向大家展示一下而已。 每逢过年过节,送茶礼是女孩子最关注的事情,大家都在心里暗暗较劲,相互攀比:谁家送了什么,送得那叫一个气派,连扁担都压弯了;谁家送得寒酸,不敢走大路,天都快要黑了才送来,女方连门都没让小伙子进;谁家的女婿一表人才,谁家的女婿贼眉鼠眼,这些都是她们在田里干活百谈不厌的话题。 那天我们在棉花地里锄草,端午节快要到了,不时有挑着满担茶礼的年青人从堤上走过,姑娘们总是会停下手里的锄头观望,然后就开始议论自己村里有谁家送了茶礼。
“春香家里的茶礼送了没有?”有个姑娘问,大家把目光都转向春香。春香低着头依旧锄草,好像什么都没听见。 我听村里人说过,春香也是很小就订了亲的,她订亲的人家在村里数一数二,男方在区里拖拉机站上班,是拿工资的。小伙子长得模样端正白白净净,村里姑娘都说,“肯定白净哒,都晒不到日头的,春香日后嫁到街上去,也不用晒日头了!” 据说春香的女婿伢送的茶礼在村里总是最冒尖的,她父母非常满意自己未来的女婿,村里的姑娘们更是羡慕不已,但春香绝口不提自己的亲事。 大家见春香不搭腔,也没继续往下问,刚好堤上又走过一个挑着茶礼的,她们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去了。 我在棉田里费劲的锄草,锄头总是不听我的使唤,看准了是一棵草,用力锄下去却把一株棉苗锄掉了,所以我格外小心。春香就在我前面不远,显得无精打采的样子,完全不像平日干活那么麻利溜刷,我赶紧把锄头扒拉几下,跟她并排站在一起。 她看见我追上来,还是不说话,有时停下锄头半天不动望着天空发呆,我也不晓得该跟她说什么,就跟她一起慢慢往前移动。 突然她转过脸来问我:“你们城里的姑娘伢可以自己说人家吧?” “说人家”! 这个词真是太搞笑了,我差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马上想到上次的教训,赶快把笑又憋了回去。 根据我的理解,”自己说人家”应该就是“自由恋爱”的意思,春香大概是想问我,城里人是不是可以自由恋爱。 那个年代是不谈爱情的,只谈革命情操,革命理想,谈情说爱是资产阶级思想。从书本上读到的爱情是马克思燕妮那样崇高伟大的革命爱情,我们望尘莫及。我们只能谈怎样努力改造世界观,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 我告诉春香,我们不说人家,我老爸老妈也没将我许配给任何人。春香疑惑地看着我说:“不说人家,那你日后怎么嫁出去呢?” “怎么嫁出去?”这个问题对于我真是太遥远了,我连做梦都没梦到过这么重大的事情。那时我16岁,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懵懵懂懂,愚昧而又迟钝。我答非所问地对春香说:“嫁出去?那总得要先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吧?”
春香接过我的话说道:“城里姑娘不用说人家?找到喜欢的人才嫁?做城里人真好!”春香最后梦呓般说了一句:“我是没指望了…..” (6) 端午节到了,尽管上面一再三令五申,不许私自杀猪,更不许私分猪肉,可是端午节在农村是个非常重大的节日,我们队长违令在半夜三更杀了2头猪,并挨家挨户悄悄地通知大家去分肉,每户5斤。我们4个知青算一户,也有5斤肉,我们像做强盗一样偷偷摸摸趁着月黑风高去把猪肉领回来,队长同时还通知说:明天端午节,休息一天不出工! 这真是让人欣喜若狂,不出工还有肉吃!我们核计了半天怎么吃肉,最后决定切大块红烧,这样最解馋,我们几个人真的是馋坏了,每天连做梦都梦到好吃的。 端午节那天风和日丽,我说我去地里挖点野韭菜烧肉,就提着篮子到村外去了。 初夏的田野很美,星星点点的野花点缀在绿色的原野上,微风吹来一阵阵清香,平日里天天从这里走来走去上工下工,怎么就没注意到这样的美景呢? 良辰美景还有肉,我的心情格外好,一边走一边哼着歌。田野里野韭菜到处都是,说它是韭菜其实长得跟小葱差不多,空心的茎叶,圆圆的白色球状的根,不一会我就挖了一篮子,准备回去了。 我突然发现前面不远的田埂上,春香蹲在那里,手上拿着一根草在发呆。我本来想吓唬她一下,临时又改了主意,喊了一声“春香姐,你在那里搞么事?” 她抬起头,看着我勉强笑了一下说:“屋里来了客,我不想回去。” 我刨根问底:“哪个来了?“ 春香低着头扯地里的草:“那个人,送茶礼来的,屋里要留他吃饭。” 我好像明白了,又好像更糊涂了,我也在她旁边蹲下来。 “春香姐,你不喜欢那个人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春香抬头看看我:“我….不晓得….” 她犹豫地看着我,好像在考虑是不是应该跟我讨论这么重大的问题。但她还是接着说:“我蛮见不得他,看到他心里就发烦。想到一辈子要跟他在一起,心里像猫爪子在抓。我就是当老姑娘,也不想嫁给他。” 我很吃惊,在农村当老姑娘是要被人耻笑一辈子的,哪家要是有个老姑娘,一家人都会抬不起头来。 春香又说:“我屋里大人都中意他,村里姐妹也眼红我,他们哪里晓得我心里其实蛮苦的。”春香的眼圈红了,她扯了一大把草,又把草狠狠地甩出去。 “那你...是不是喜欢别的人了?”问题刚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太冒失了。 “没有没有,我哪个都不喜欢,”春香赶紧说:“我就是不想见他!” 我们都沉默了,我无法窥见她隐秘的内心世界,也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我们呆望着前方,春香的眼睛空洞而茫然。 仿佛过了很久,时间似乎凝固了,田野显得那么空旷寂寥,一只乌鸦飞来,“呱”地一声打破了沉寂。刚出来时的美好心情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觉得莫名的难过和惆怅。 我猛然想起我还要赶紧回去,他们还等着我的韭菜烧肉呢!我站起来对春香说:“春香姐,你不想回去就到我们那里吃饭吧,我们今天烧了肉。” “嗯!”春香嘴唇没动的哼了一下,声音低的几乎听不见。 那天春香没有来。后来我们听村里人说,端午节那天她跟家里大闹了一场,她要父母去退亲,她坚决不嫁那个人。她妈妈气的直骂她中了邪,说她天天跟城里来的几个青年知识混在一起,心野了。她不能跟我们比,我们是金命,她是土命,这样的好人家都不想嫁,还想嫁给什么人?再说人家送了十几年的茶礼,眼看媳妇就要娶进门了,现在翻悔有那么容易么?以后全家人还怎么在村里做人? 可是春香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是反复说她就是不嫁那个人。老实巴交的春香爸爸气的实在没法,狠狠地扇了春香一个耳光。村里人说,春香从小长到大,她父母连重话都没说过她,更别说动她一个手指头了。 端午节过后的好多天,我们都没看见春香,听说她生病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田里碰见了她,她看见我们,还是微微一笑,可是那笑容里却增添了许多苦涩。 从那以后,春香几乎不到我们的知青屋来了。 (7) 那年夏天,江汉平原异常闷热,每天去田里出工回来都会浑身湿透,汗气逼人。天门河水就在我们的房子下面,波光粼粼闪着清凉的光。村里的男将还有小屁男孩都在河里“打鼓泅”(天门话“游泳”是“打鼓泅”,我觉得蛮形象的。)可是没有一个姑娘媳妇会到河里游泳,哪怕只是到水里去泡一下凉快凉快都不行,这是那里的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姑娘媳妇要是也下河跟男将一起玩水,那就坏了一方规矩了。 我们几个学生伢不信这个邪,尤其是我最喜欢游泳。读小学的时候暑假我会买“滨江游泳池”的月票,每天下午去游泳。后来搞文化大革命不上课了,我们就更加嚣张,天天拿着哥哥郭小宁画的假月票跟邻居一起到武大东湖体院游泳,有时一去就是一天。现在眼前就是天门河这么好的一个天然游泳池,碧绿的河水清澈透明,这诱惑实在太大了!要我不下河游泳,这怎么可能?我们小组另外两个女生在我的鼓动下也蠢蠢欲动。 但是我们也不想让村里人晓得,总是等到天黑以后才悄悄下到河里,尽量不搞出太大的动静。村里人家大都住在湾子里,天黑以后没什么人到河边来。堤上的房子只有几栋,我们的知青屋最靠近河边。每天我们蹑手蹑脚下到河里,游上一阵,顺便把衣服也洗了,等到凉快了我们就上岸,一打两就,衣服洗好了,回来把湿衣服换下来,澡也不用洗了。所以每天收工以后我们就盼着天黑,到河里游泳是我们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光。 天门河水沁凉沁凉的,河里有鱼,如果站在水里不动,就会有小鱼游过来啄我们的脚趾。我们知青小组有个绰号叫麻雀的女生不会游泳,她自己说她是 “水上警察”,当警察的主要是站在那里,当然被鱼啜到的机会就更多,那天她的小脚趾头被小鱼啜了一下, 于是她惊叫起来,她的绰号是麻雀,可想而知那声惊叫真的是惊动了四面八方,我们被村里人发现了。 “女青年知识到河里打鼓泅”的消息传得飞快,堤上很快就站满了围观的人,他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搞得我们狼狈不堪。 当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河里爬上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春香。暮色中,她的白牙齿闪了一下,我知道她在对我笑。 “你们胆子真大,老人说这河里有水鬼涅!”她小声对我说。停了一下,她又补充了一句:“专门捉十七八岁的姑娘家!” 我把湿淋淋的头发抹了一把,甩下一串水珠:“我们不怕水鬼!”我附在她的耳边故作神秘地说:“水鬼不敢捉青年知识!” 白白的牙齿又闪了一下。 (8) 春香要出嫁了,听说是男方催的很急,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春香家里也唯恐夜长梦多,愿意早点把喜事办了,早嫁早安心。春香9月份满十八岁,所以日期初步定在秋收过后的冬闲日子,具体哪天还要请高人计算,挑选一个黄道吉日。 我们很久没有见到春香了,田里干活她也很少去。这一带的姑娘们出嫁前都是要躲在家里一段时间不露面的,忙着纳鞋底纳袜底做嫁衣准备出嫁的行头,所以谁也没有在意。偶尔提到她,大家只是说,这村里又要少一个“坛子”了。 转眼已是深秋,天黑的越来越早,吹拂在脸上的风也带有明显的凉意,堤边上不再有人乘凉,村里东家长西家短的事情我们也很少听人说了。 我们小组的男生去区里办事,带回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要招工了!招工,那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回到武汉,回到我们熟悉的城市,回到从小长大的温暖的家。消息虽不确切,但我们还是异常兴奋,如同在沙漠里经过长途跋涉的人突然望见了一叶绿洲,又鼓起了前进的勇气。生活中总是要有希望的,有了希望就会有信心,尽管有时希望是这样的渺茫。 我们在煤油灯下兴高采烈地谈论着,那个男生唱起了在知识青年中流行的自编歌曲“怀念江城”,我们在一旁敲碗为他助兴。接下来又是畅谈:仿佛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学生时代;夏令营的篝火;篝火旁的朗诵;大串联的洪流;步行长征的红旗……青春和理想,曾经一度像团迷雾般看不见摸不着,而现在又似乎清晰可见触手可及了。 不知什么时候,春香来了,她静静地靠在门框旁一动也不动。 我们看见她,都有点意外,赶紧招呼她进来。 “你们要走了吗?”她在门口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进来。 她瘦多了,煤油灯下,她的皮肤好像也变得白净了。 “哪里,还没有影子的事情。”我们不想过早把事情传开,赶紧向她解释。 “你们终归是要走的,我早就晓得,你们不是这里的人。”春香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刚来的第一天在天门河岸边有关扎根的一段对话和她的灿然一笑。 她心绪不宁地走到桌边,拿起我们放在上面的一本书胡乱翻了几页,又放下了。接着她走到墙边,那里贴着一张芭蕾舞剧《白毛女》的剧照,她凝视了半天。 她好像觉察到她的到来破坏了我们刚才的欢乐气氛,歉疚地说:“我走了!”走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眼里闪出一丝依恋的神情。 我追到门口挽留她:“春香姐,你再坐一会吧!” 她摇摇头说:“不了,我要走了。”她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终于没说,只是笑了一下。不知为什么,这笑容竟使我觉得有点凄凉。 这是春香给我的最后一笑。 (9) 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听说春香在天门河里淹死了。 村里乱成一团,堤上挤满了人,春香的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春香已经被捞上来,她静静地躺在那里,脸上似乎还留着那淡淡的微笑。 我们好不容易才听清楚事情的大概:春香的爸爸妈妈一大早就出早工去了,春香弟弟听见姐姐开门出去。等她爸爸妈妈回来,没看见春香。然后有去河边挑水的人说看见春香洗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河边,他们赶紧到河边去找…… 一切是这样简单。 春香的妈妈还在撕心裂肺地哭着:“春香啊,你不跟妈说一声就走了,你好狠心啊!你这些日子不快活,妈晓得,可你不该就这样走,不该啊!” 春香的爸爸蹲在一旁,双手捧着脸,泪珠从他那粗大的手指缝里往下流淌。 一位妇女抹着眼泪连连说:“春香是个好姑娘,唉,年纪轻轻的,造孽呀!” 春香就这样走了,连同她那淡淡的微笑。她连死也不愿惊动别人,静静地独自一人,如同她活着的时候一样。 天门河水依旧流淌着,不时有浪花拍打着岸边,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春香下葬了,她的新坟在那姓刘人家的坟冢中间,很快上面就长满了草。 春香死后一个月,村里人纷纷传说,在她死的头一天,她妈妈看见一只黑猫从春香房间的窗户跳出去,据说那是专门来勾春香的魂魄的。 也有人说,春香是被河里的水鬼拉下去的,甚至还有人煞有介事地说亲眼看见春香手腕上有被水鬼捏过的青痕。 我却不会忘记春香给我的最后一笑,那无限凄楚的笑…… (10) 直到至今,我还是不很理解,为什么春香竟那样轻易地结束了自己青春的生命?是心里有巨大的无法述说的痛苦?还是实在无力反抗命运的安排?或者,仅仅是由于不小心,失足滑进了天门河中? 我常想,倘若春香活到现在,她一定是个操劳的农家妇女,也一定是个贤淑的母亲了。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是个十八岁的少女,温柔,恬静,脸上有着淡淡的微笑。 天门河,愿你能安抚春香的灵魂,洗净她的痛苦…… 平平
后记:这是一篇旧作,大约30多年前写的,写好后就搁置在那里了。那时有关春香的回忆还是十分鲜活的,历历如在眼前。时隔30多年再读这篇文章,春香又从记忆深处向我走来,她仍然是十八岁的少女,脸上依然是纯净的微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