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被消弭的声音,复原被剪除的视角,“即便功败垂成”|拉纳吉特·古哈逝世

拉纳吉特·古哈
据报道,印度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 (Ranajit Guha)于4月28日去世。 拉纳吉特·古哈是后殖民主义与庶民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也是《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创刊编辑,他的著作包括《孟加拉地区的土地产权统治》,已被公认为经典的《殖民地时期印度农民起义的基本方面》,《没有霸权的统治:殖民地时期印度的历史与权力》,以及《历史的低语:论文集》。
三辉图书出版的《少数人的恐惧》收录了古哈的两篇论文《钱德拉之死》和《迁移者的时间》。“《钱德拉之死》基于一本早期孟加拉信札集中收录的法庭证词片段。对非传统证据的探究是为了寻找庶民主体能被视为自身代言的原始资料。”它讲述的是一个印度少女服用打胎药身亡的故事。关于凶手是谁,法律与审判程序凭借自己的权威重新组织了证词的顺序,给出了一个答案;但是历史学家重新翻看文献,又在其中找出了另一重现实:少女钱德拉调动她“所能动用的可怜资源,动员她的女眷们,以她自己唯一可能的方式同父权做斗争,结果悲剧性地死去”。最后在法律干预的逻辑之下,“一位关怀体贴的妹妹成了凶手,这场悲剧中的所有行为主体都成了被告”。钱德拉之死成了国家与社群较量的话语场域,国家已经先行抵达,历史学家试图完成的则是打捞被 消弭的声音,复原被剪除的视角,“即便功败垂成”。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推文摘自《少数人的恐惧》,“钱德拉之死”。
“天刚蒙蒙亮我就又把药打成糊,递给了钱德拉。可这对打胎无济于事。第二天,我又和母亲还有钱德拉一起去见了卡利·巴哥迪。他给了我们一种草药,得一天吃三次,而且要和horituki(一种有药效的野生水果)一起服用;还给了两片在石灰水中稀释过的bakhor guli(一种水稻和草药混合成的用以引产的制剂)。Choitra(孟加拉邦纪年的第12个月,大致对应3月的下半月到4月的上半月)12号那天,我约莫在晚上第二个pohor过一刻(午夜的12点3刻)的时候又亲手准备了一些糊状的药,喂了一剂给钱德拉。大约同一时候,胎儿打下来了,掉在地上。我的母亲用一些稻草拾起了沾满血迹的死胎,把他扔了。即便在那之后,钱德拉的肚子仍旧愈加疼痛,在天亮前四五个dondo(日出后不到一小时),她就离世了。之后,钱德拉的尸体就被我的哥哥加亚拉姆、他妻子的兄弟和我母亲的兄弟霍里拉尔埋在了[河的]拐弯处。我把药递过去本以为可以终结她的怀孕,却没意识到这会害死她。”陈述结束。

图源:纪录片《印度的女儿》
其他的被告因这份证词被捕时,死者钱德拉的母亲巴加波蒂·查什恩也拿到了一份为她写的证词,书写原则与布林德拉的那份一致,上面进一步宣称道:“去年Phalgun(孟加拉邦纪年的第12个月,大致对应2月的下半月到3月的上半月)末尾的时候,玛加拉姆·查沙来到我的村子里告诉我说‘我惹祸上身了,四五个月前,我和你的女儿钱德拉·查沙尼私通,结果她怀孕了。把她带回你家,给她预备些该吃的药。不然的话,我就要把她安置到bhek去了’。两天后,我让我的女儿布林德拉和我姐姐的女儿朗格·查沙尼到巴班伊布尔去把钱德拉接回来。当天晚上天黑后大约一个prohor,她们和钱德拉·查沙尼一起回到了马伊格拉姆。朗古说钱德拉的婆婆斯里莫蒂和她婆家姐姐的丈夫玛加拉姆·查沙给了她们一个黄铜的罐子和一只铜质地的碗[用以支付]买打胎药的费用。”陈述结束。
而被告卡利查兰·巴哥迪在证词中说道:“距今年Phalgun末尾还有五天还是七天的样子,那天我正待在河岸边的菜地里,快到第二个dondo的时候,朗古·查沙尼走近我说‘请到我家来一下,等你来了,我会把一切该说的都告诉你’。第二天,我来到了邦什·巴哥迪在马伊格拉姆的家,在那儿,却没见到朗古·查沙尼。就在我要回家的时候碰见了巴加波蒂·查沙尼。她告诉我说‘我的女儿钱德拉·查什尼已经怀孕三个月了,请让我们拿一种药来终止这次受孕吧,我们会送给你一只罐子和一只碗的’。[对于她的请求]我没有同意。又过了一天,天刚刚亮了一个半dondo的时候,我还在菜地里,之前的巴加波蒂·查什恩又来找我,还跟着锡姆拉村子里一位上了年纪的农夫。他是巴加波蒂儿子的老丈人,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巴加波蒂说,‘请给我们一片药吧,把胎儿打下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会付现金的。’因为当天我身上没有带着打胎的药,我告诉巴加波蒂说,‘请明天到菜地这里来见我取药,不必麻烦你的亲家再跑一趟了。’第二天,我还是在我的菜地里。中午的时候,巴加波蒂带着她的女儿钱德拉·查什尼过来了,前一天巴加波蒂的亲家也答应要付现金,正因为这样,我为拿来的药要价。死者钱德拉给了我一派萨(paisa,一枚相当于0.64卢比的铜币)。我收下了那枚派萨,安顿她们在菜地坐下之后……”[公元1849年]
***
从再明显不过的意义上来说,这(证词的顺序)与刑罚的步骤是对应的,起初是一份导致抓捕行动的证词,其他的证词又接踵而至。在我们的文本中,法律的权威之声突然插入前两段陈述中,如是说道:“其他的被告因这份证词被捕时,死者钱德拉的母亲巴加波蒂·查什恩也拿到了一份为她写的证词,书写原则与布林德拉的那份一致,上面进一步宣称……”然而,不甚明确的是,事件的实际次序和文献中所呈现的不一致。从我们掌握的信息中显而易见,一听到女儿怀孕巴加波蒂便采取了行动,然后就是和卡利·巴哥迪交易,紧接着就是布林达的派药和她姐姐的死讯。然而,证词的顺序却是布林达要第一个叙述。结果,“讲述”便从中间开始,描述了她在故事中的片段和钱德拉的死,之后又通过其他两份描述——巴加波蒂的和卡利的——回溯式地追溯了它的步骤来填补背景信息。 换句话说,为了迎合法律干预的逻辑,文献中的叙事违背了事件发生的真实次序,使得死亡成了谋杀,一位关怀体贴的妹妹成了凶手,这场悲剧中的所有行为主体都成了被告,而他们在悲痛状态之下的陈述也都成了ekrars(供述并确认罪行的法律术语)。 如此构建,一段真实历史经历的母体被转换成了抽象的法律性的模型,以至于国家的意志可以被用来逐步地渗透、重组,并最终控制人民大众的意志,这与引入神灵的意志,把它强加于纯粹的人类命运如出一辙。
这样假设的结果便是将我们面前的证词顺序同化到另一种次序中,即法律和秩序。在所有可能的关系里只选择其中之一,将它们的内容和表达联系起来。并且认定那种关系——那种独特的内涵就是已经被划定为犯罪的事件的真相。正是那种凌驾于其他之上的内涵意义将从个体——妈妈、妹妹和邻居——那里记录来的言说的多样性糅合成了一套呈堂证供,并且由此允许国家的洪钟之声将在这里言说的卑微的农民的声音消弭在声声的哭诉和低语之中。要尝试并且表达,后者便要公然挑战抽象的单音性主张。它顽固地将这种多面的、复杂的人类困境的织体命名为“案例”。而这个词通常意指一个“事情发生的实例”或者一份“审判中的事实陈述”,这便授予了这几段陈述这样的功能,把死亡仅仅描述为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个缺乏任何其他裁定而只是在审理中的事实。仿佛在这样的描述中,意志和企图没有丝毫的空间,所有说出的话都旨在论及一个没有主体的事件。“罪犯的特殊意志”,根据黑格尔的观点,是“侵害具有的唯一肯定的实存”。在阅读这些ekrars时,承认有犯罪行为而排斥所谓罪犯的“特殊意志”,并用“单一事态”空洞的事实性来取代钱德拉受“侵害”的“唯一肯定的实存”,这会把叙述的创作者和他们的经验排除在历史的门外。 相较之下,将这些陈述作为档案文件来阅读便是将其升华为文本的场域,为了历史奋力去重塑一段掩埋在被遗忘的过去的裂隙中的经历。

图源:纪录片《以火书写》
那样的奋力争取丝毫不亚于两种政治间的较量。每一方都将其作为尝试的目标,并占用钱德拉的死作为话语的场域——一方代表国家,而另一方代表社群。不过,事实却是作为国家特使的法律已然先于历史学家到达了这片场域,并声称这是自己的地盘,将事件指定为“案件”,死亡为“谋杀”,而描述的陈词成了“ekrar”。 如此霸占的结果即是将事件置于社群生活的视角遭到剪除,在那里,多重的焦虑和介入赋予了其真正的历史内涵。如若通过解读来抗议这样的诡计,反对将这些陈述同化入法律的层层程序,而是将其视作一种记述,一种有关巴哥迪种姓的一家人齐心协力共度危机的记述,那么即便功败垂成,其中的一些视角也有可能被复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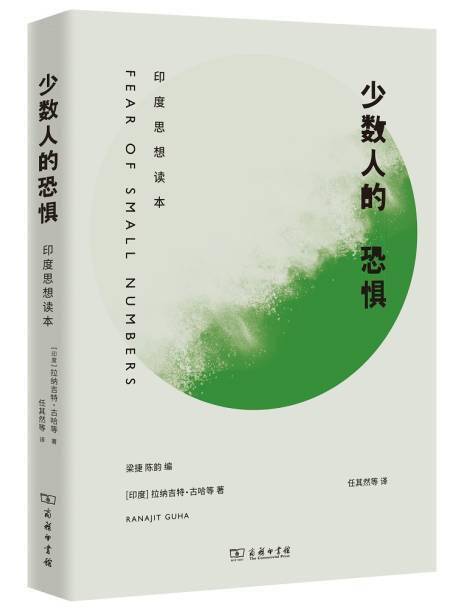
[印度] 拉纳吉特·古哈等 著
梁捷 陈韵 编 任其然等 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选编了包括阿尔君·阿帕杜莱、拉纳吉特·古哈等当代印度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思想家的代表性研究论文,覆盖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他们的研究是近几十年印度思想研究方面最突出的工作,既与过去的印度古典研究有联系,更与当下印度思想的发展有关,凸显出印度独有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