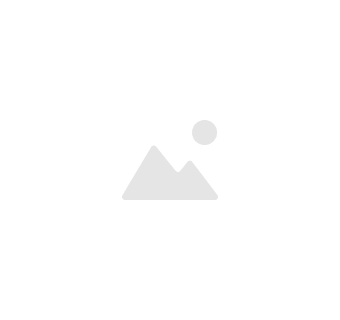也当一回标题党,呵呵:)
其实,文怀沙的年龄,关我什么事?不过是当我看见朱季海的名字卷在这段公案中时,想起了一些往事。
现如今流行用“最后”作修饰语,比如“最后的贵族”、“最后一个太监”、“最后的母系氏族”、“最后一个莫西干人”、“最后一个女土司”、“最后一个地球公民”……还有“最后的沃氏三趾鹑”什么的。如果用“最后”去修饰朱季海,那他真就是姑苏城最后一位隐士了。所谓的“大隐隐朝市”,说的就是朱大隐士。
朱季海是颇有些林下之风的,虽不像竹林七贤那样宽袍广袖、飘逸如仙,但时出狂放之举,若在金庸的小说里,他就是“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黄老邪,或者跟黄蓉没大没小的洪七公,反正有关他惊世骇俗的段子,着实在城里留下了一长串。你跟他在一起,千万不可遵辈份礼法,若尊称他“朱先生”、“朱大师”、“朱老”……,你就等着他瞧你不入流吧,反而是直呼“朱季海”、“老朱”的,他听着欢喜。可惜朱季海生错了时代,要是处在一个风流清逸的年头,不知该有多么肆意酣畅呢。
知道朱季海是因为他那本《楚辞解故》(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当时我不知中了什么邪,某一门课的学期论文题目,选了汉代王逸的《楚辞·天问序》来自讨苦吃。遇到文学院的吴企明先生,问我近日忙些什么,我就“呵壁”、“问天”地大诉其苦。吴先生是苏州人,研究唐代文学的,一口吴侬软语,平时连上课也不肯说普通话,害那些外地来的学子们吃足苦头。“馁(你)去寻《楚辞解故》来看看,朱季海先生写咯,朱老学问呱呱叫,章太炎先生个得意门生,鲁迅先生个同门,俚人就落了苏州,就是《楚辞解故》不晓得馁阿读得懂”。
等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薄薄一本《楚辞解故》借到手时,才知道上了吴先生的当。天地良心!《楚辞解故》我怎么可能读得懂呢?别说我读不懂,恐怕整个文学院也没几位老先生能读懂。因为这本被誉为“学界天书”的小册子,是以楚语解楚辞,世所少见,正经比屈原的《天问》还天问啊。当时心里就嘀咕,最合适的读者,怕是非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莫属了。后来才听说,谁能把朱季海这本书看明白,谁就已进入中国楚辞研究前列了。
我把《楚辞解故》像烫手山芋一样还掉,但从此记住了朱季海这个名字。可等我真的见到朱季海本人时,却又有眼不识金镶玉。
那次是在小马师兄家玩,那时小马师兄还住在钟楼附近一条小巷子里,一间平房,正对着一个布满青苔的天井小院。师兄也是个散漫随意之人,跟他一起喝茶聊古籍版本,时间“嗖嗖”地就过去了。然后就有一老者,在门首探头探脑,形迹可疑。师兄见了,走过去招呼他。老者看我一眼,嗫嚅道:“啊,你有客人呀,我等等再来”,语未毕,人已飞速消失。
我问师兄刚才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是谁,很像是来借钱的。“朱季海啊,你不认识他?江湖上名头很大的”,师兄听见我的评语顿时跌足狂笑,“我一定要把你这句鬼鬼祟祟转告他”。
“朱季海?《楚辞解故》!”我飞奔而出,可是哪里还有什么人影?
后来一次是在校门口的“望星桥”堍,小马师兄和他的忘年交朱季海坐在卖生煎包的铺子外面,一条乌黑油腻的长凳,一老一少两个顽童,大有风尘隐士的模样,在午后的阳光里聊得正开心呢。我骑车经过他们时,师兄冲我招招手,诡诡一笑。我深怕我的出现提醒师兄转述那番“鬼鬼祟祟”的评语,于是把脚踏车踩得跟风火轮似的,一溜烟远了……
回到文怀沙大师的年龄,果然,94岁高龄仍不愿被体制招安的朱季海第一句话就说,“追问年龄是一种恶习,这是连小女孩都懂的事。我们认识几年了,我也不知道你年龄,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这番话是对追问他的傅奇说的,几年前傅奇在苏州城里办了所“复兴私塾”,请朱季海当顾问,又是一个醉心古典文化的“痴子”,呵呵。
傅奇的文章在这里/>,如有兴趣大家自己看吧。
94岁高龄的朱季海先生
倒是另有一篇好文要借此机会全文转贴,那是俞明的《痴子》,写朱季海写得入墨三分,网上绝搜不到(当然,今天之后可以google到豆腐庄来了)。几年前我曾为美东一家周报客串一个文化版的编辑,为了介绍朱季海,从藏书中找到这篇《痴子》,一个字一个字敲键盘,打字打到手脚发软时,过去的一点一滴重回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