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全球暴力渐行渐远,唯中俄逆流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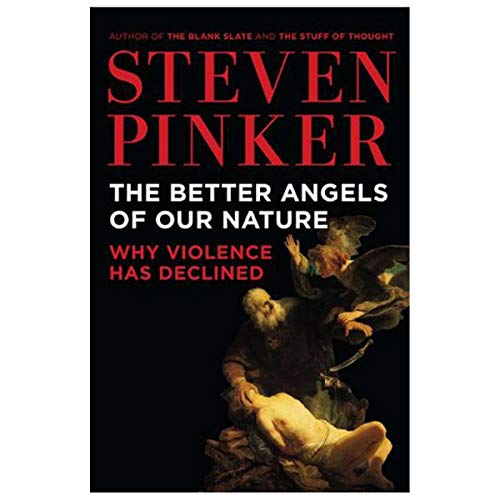
斯蒂芬·平克是心理学和语言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入选《时代周刊》世界有影响力的百人、《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和《前景》杂志的全球思想家名单。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涉及历史和心理学。书中直言人类历史在进步,暴力下降就是历史进步的度量。全书引用了很多数据说明历史上暴力的确在降低并解释了暴力降低的原因。
五千年来人类历史有五大趋势,都呈现了暴力在降低。考古发现史前因暴力冲突而导致死亡的比例约为15%。国家建立之后,暴力冲突的死亡下降。即使在有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战争造成的死亡只占全世界人口的3%。20世纪下半叶,人类史无前例地避免了大国之间的战争,实现了一个相对长期的和平。第二个趋势是个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在降低。凶杀案的比例从欧洲中世纪的每10万人每年超过100件,下降到了1950年代的每10万人0.8件。第三个趋势是酷刑和死刑的下降,人祭和猎巫等习俗的消灭。平克称之为“人道主义革命”。第四个趋势是种族屠杀的减少。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震惊了世界。1948年,联合国批准了《关于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公约》,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种族屠杀视为犯罪。第五个趋势是权利革命,包括种族,性别、儿童、同性恋、动物等权利的重大改进。
三个原因导致暴力下降。第一是,欧洲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采邑林立的无政府状态后,出现了真正的利维坦。15世纪,欧洲有500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主要是领主封地和小公国),17世纪 “三十年战争”时期是500个政治单元,19世纪初拿破仑时代是200个政治单元,而在1953年,欧洲只剩下不到30个政治单元了。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程度比部落形态的社会要低得多。即使在战祸最深重的年代,现代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也还不到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死亡率的1/4。这是霍布斯理论,利维坦即国家为了消除无政府状态下的暴力而产生。
公元900年至今,欧洲著名的冲突有2314场。附表列出了按死亡人口排列的21个世界事件。最后一列是按死亡率的排名(分母是20世纪中叶的世界人口)。死亡率高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是:中国王莽时期、三国、罗马衰亡、安史之乱、成吉思汗、中东奴隶贸易、帖木儿、大西洋奴隶贸易、明朝灭亡和征服美洲。政权大屠杀死亡中有四分之三是四个政府造成的,苏联: 6200 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3500 万人,纳粹德国: 2100 万人,1928-49 年的中华民国:1000 万人。另外 11% 的人被 11 个政府杀害,其中包括日本帝国的 600 万人、柬埔寨的 200 万人和奥斯曼土耳其的 190 万人。极权政府要对1.38亿人的死亡承担责任,占全部政府造成的死亡的82%。近现代史上,最突出的杀人大国是中国和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说,杀害几百万人,你需要一个意识形态。过去500年内,所有最具破坏力的冲突都不是资源驱动,而是意识形态驱动的,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乌托邦导致大屠杀的原因是功利计算。当你假定有6亿人的生命可以得救,那么死上几百万人似乎还是值得的。希特勒在1913年读到马克思的作品,尽管他仇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他的国家社会主义乌托邦理论里,他只是用种族置换了阶级。
悖论是国家形态社会下暴力减少是普遍规律。但是中国自秦朝起就建立起福山所说的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仍然有着世界十场最高死亡率冲突中的五场,且最近的两代中国政府都要对治下的高生命死亡率负责。以国家名义实行的大规模暴力也许是中国的特色。另一个推断是在治理好的国家,固然暴力会降低。但国家形态下不可避免的改朝换代可能带来更加惨烈的暴力和死亡。而中国历史中,这样的改朝换代又特别多和剧烈。
康德的永久和平条件:民主—开放经济—国联。(1)各国都是民主政体(共和制)。因为民主的基础是非暴力的,通过共同接受的法治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民主国家在与其他民主国家交涉时将这一原则外部化。民主政体倾向于避免战争,民主国家领导人要对人民负责,他们不太可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荣耀,牺牲人民的鲜血和财富,发动愚蠢的战争。在专制政体下,君主很可能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发动战争。如果权力在民,他们就会考虑为什么要在愚蠢的国际战争上浪费钱财和生命。与个人崇拜、输出革命和沙文主义使命不同,每个民主政体都建立在同样的理性基础之上,所以每个民主国家都知道其他民主政体如何运作。根据霍布斯,担心对方先下手的恐惧让双方都有先发制人的意愿,而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推定信任,能够将这种恐惧消灭在萌芽状态。民主国家的愚民少,不好战。不会以强硬民意和民族主义口号绑架国家。 (2)“以自由国家联盟为基础制定国际法”的国联,而不是联合国那样的所有国家的空谈机构,一件好事都干不成。(3)一个自由市场国家的透明度和可理解度能够让邻国确信它不会进入战时体制。在市场经济中,政客的权力受到控制生产手段的股票持有人的约束,他们会反对扰乱国际贸易。对于领导人追逐个人荣耀、宏图伟业的个人野心,市场的制约就是一道紧箍咒。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革命。古时候,人们对生命的价值评价很低,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痛苦和死亡。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时,食物更好了,身体更健康,起居更舒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以及别人的生命,也都更有价值了。那些率先废除严刑峻法的国家,比如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确实位居那个时代最富有的国家之列。而在今天世界上那些贫困的角落,我们继续能看到奴隶制、迷信杀戮和其他野蛮习俗。
第三个原因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和之后的人道主义革命。许多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斯宾诺莎、笛卡儿、洛克、休谟、康德、亚当斯密、麦迪逊、杰斐逊、汉密尔顿和约翰·米勒,共同构造了古典自由主义或启蒙人文主义。启蒙人文主义的起点是怀疑主义和理性。怀疑和理性动摇了中世纪的神权中心和宗教蒙昧主义,推动了以生命而不再是灵魂,作为道德和价值轴心的转换。人们更相信自我或自我意识。追求自己的欢愉,包括感官的(饮食男女),和精神的(爱、知识和美感)。平等理念的普及和个人主义、自我意识的苏醒,让人追求普世的人性和人权。启蒙人文主义推崇生命至上和人道主义,完全不涉及宗教和任何无助于人的实现的价值观念,比如国家的荣誉和威望、民族主义或阶级的声誉;团体和党派的尊严,以及其他一些神秘虚幻的东西:使命、辩证法和斗争。人道主义革命的主要动力,平克归功于印刷技术、书籍报刊的普及流通以及书报读者的大幅度增加。18世纪是小说史的转折点。小说自此成为一种大众娱乐,不再拘泥于讲述英雄、贵族和圣徒们的业绩,而是再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以及奋斗和失意。阅读帮助人们设想他人的经验与感受。读者站在作者或主角的立场观察世界。去看、去听、去体会并未亲身经历过的场景,走进他们的心灵,分享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和反应。共情是导向同情的自然通道。人们对自己的同类开始有更多的同情心,将生命和幸福作为价值的中心。形成人道主义或人权的苏醒。
中国号称“礼仪之邦”,以伦理道德约束人民。但历史上战争,杀人,酷刑,暴力都在世界上排名靠前。外交部发言人争当战狼,民间有暴戾之气。邻国地震,举杯遥庆;世界战端,幸灾乐祸。原因之一是中国历史缺了启蒙人文主义这一课,民众文盲半文盲率高,读书少,社会缺乏人文主义精神。加上中共执政以来,以阶级性排斥人性,以民族仇恨煽动爱国主义。造成大众三观中缺少人性和人道主义成分。历史上,在政权杀人方面,中俄独领风骚。而今天两国都成为对世界和平的现实威胁,因为它们都有改变世界现存版图的妄想。也是康德理论中挑起战争的极权国家。
“人权观察” 称美国在2008年轰炸塔利班的行动中恪守人道主义原则,为“最低限度伤害平民的良好记录”。2004年至2010年间,阿富汗战争的平民死亡大约是5300人,其中80%是被塔利班而不是联军所杀害的。对于这样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而言,这个水平相当低——相比而言,越南战争中至少有80万平民死于战火。政治学家维克托·阿萨尔和埃米·佩特审视了1950年以来124个国家中337个少数族裔的状况。美国和欧洲的少数族裔的处境最好,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官方的政策歧视。在亚洲、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中东地区,虽然自冷战以来情况都有所改善,但少数族裔仍然受到合法的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