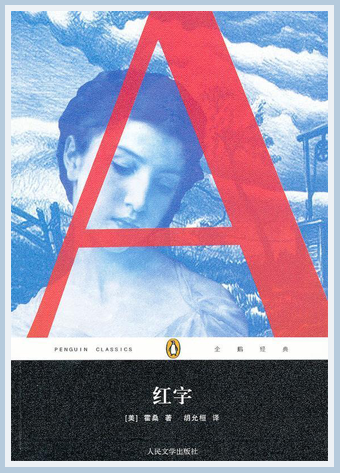| ||
|
《红字(缩写本)》 文:(美)纳撒尼尔·霍桑 诵:张家声
差不多在两个世纪以前,一个夏天的早晨,在牢狱前的草地上,拥聚着好大一群波士顿市民。他们的眼睛全都死盯住铁甲板的橡木门,狱门从里面打开了,首先,像一个黑影浮现在阳光中,出来的是那狱吏的狰狞而尴尬的面孔,他的相貌象征着清教徒法典的全部的铁面无情。 他左手举着官杖,右手抓着一个青年妇人的肩膀,把她拉向前来。到了牢门的门槛边儿,这个妇女推开了他,自动迈步走到门外。这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约有三个月的婴儿,她下意识地把那个婴儿贴在胸怀,以遮掩那缝在衣服上的标记。不过她马上就明白,这孩子本身也是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拿他来掩饰另一个标记是不高明的。因此,她又把婴儿撑在胳膊上,面孔发着烧。现出高傲的微笑,用一种盛气凌人的眼光环视一遍同城的居民和邻人。 在她衣服的胸部,现出了用精美的红布制成的A字,四周有金线刺绣的奇巧花样。 这时狱吏叫道,“让开路,诸位让开一条路,我可以答应你们,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从现在到午后一点钟,好好的参观白兰太太的红字。” 旁观的人群立刻让开了一条小路,海丝特·白兰平静地走到市场西端的绞刑台边,登上木梯,站在一人高的台上。 她蓦地在人群的外圈辨认出一个人来。他的身材矮小,面孔多皱,可是还不能成为老人。虽然他穿着许多的衣服,但海丝特·白兰却明白的看到,这个人的左肩是比右肩高的。当他看见这个瘦削的面孔与略有残缺的身体,她用力把婴儿抱紧,使孩子发出哭声。 当那个男人发觉海丝特·白兰像是已经认出了他的时候,他缓慢地举起一个手指,在空中做了一个手势,又把手指压在唇上。然后拍拍身边的一个市民恭敬地问,“好先生,我请问你这个女人是什么人?把他搁在这里受侮辱是什么缘故?” “朋友,你一定是个外乡人。”那个市民答道,“不然,你必定早就听见过海丝特·白兰太太的丑事了。她在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教区里闹得满城风雨。” “你说对了,我是一个外乡人,在南方异教徒的居民间被囚禁了许久,现在到这里来找人赎身,你肯将这个女人的事告诉我吗?” “那个妇人是某一个学者的妻子。那个学者原籍英国,一向住在阿姆斯特丹,好久以前决心移居我们这儿。他先送太太过来,自己留着处理一些未了事务。快两年了,那位白兰先生毫无消息,从此,那位年轻的妻子便做了坏事。” “那么,那个孩子的父亲是什么人呢?” “说真的,朋友,那是一个谜。孩子她太太不肯讲,也许那个罪人正在此地望着这凄惨的光景啊,哎,可怜的女人,论罪那是要处死刑的。当局慈悲为怀,只判她在绞刑台上站三个钟头,此后她必得在胸上带上耻辱的标记。” “好聪明的裁判啊。”那外乡人垂头深思着,“这样,她将成为罪恶的标本,直到那个丑恶的字刻在她的墓石上为止。” 绞刑台上方传来威尔逊牧师的呼唤,人们发现露台上除了他以外,还站着贝灵汉州长、年轻的丁梅斯代尔牧师和其他一些可敬的人物。 那老牧师说,“海丝特·白兰,你是指定在丁梅斯代尔牧师宣布的教堂里听讲的人。因此,我好不容易说服我这年轻的兄弟,当众来追究你罪恶的灵魂。” 贝灵汉州长接着说,“善心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你对这个妇人的灵魂要负重要的责任,你应当叫他公开招认。” 群众的眼光全都集中在丁梅斯代尔牧师身上。丁梅斯代尔牧师是一个青年牧师,英国一个有名的大学校出身,他的善于辞令和他的宗教热情早已保证他要得到显要的位置。此时他垂着头,像是在默默地祈祷。接着,就走向前来,他凝视着海丝特·白兰的眼睛。 “海丝特·白兰,供认吧,供认出你共同的罪人和共同的受难者。虽然他将从崇高的地位上跌下来,同你一起站在耻辱的刑台上,然而总比一生隐藏着一颗罪恶的心要好一些。” 海丝特摇摇头。 威尔逊牧师声色俱厉地叫着,“女人,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来!那样可以去掉你胸上的红字。” 海丝特·白兰回答,“绝不会的。”并不看威尔逊先生,却一直望着那个青年牧师深遂而烦忧的眼睛,“那烙印太深了,你们除不掉它的,但愿我能忍受住他的苦痛,以及我的苦痛。” “说出来,女人!”一个人从人群中走向台边,声音冰冷,“让你的孩子有一个父亲!” “不!”海丝特面色变成死灰,可是仍然答复了那个十分熟识的声音,“我的孩子必须寻求一个天上的父亲,她永远也不会认识一个世上的父亲。” 海丝特·白兰转回监狱之后陷入神经激动的状态之中。狱吏带来了一个名叫罗格·齐灵渥斯的医生,他就是那个外乡人。孩子一见到他,马上静默了。原来这位医生就是海丝特·白兰的丈夫,在海上遇难,被印第安人俘虏了。 他说道,“我们彼此害了对方。首先是我害了你,我把你含苞的青春和我的衰朽结成了错误的关系。我不想报复你。但是,那伤害我们两个人的男人是谁呀?” “不要问我。” “你不愿泄露他的名字吗?不过,他仍然逃不出我的手掌。”他自信地微笑着,“不准泄露我曾经是你的丈夫,尤其是对那个男人。不然,他的名誉、地位、生命都在我的手心里。” 海丝特惊恐地回答,“我愿像保守他的秘密一样,保守你的秘密。” 海丝特出狱之后,带着她的婴儿在远离人群的一间小茅屋里住下,靠手工刺绣维持生活,而她自己仍过着简朴刻苦的生活。她把节省下来的资财都用于施舍,尽管那些贫苦的人常常羞辱她、唾弃她,她胸前的红字好像给了她新的启示。表面假装的贞洁只是一种欺骗,如果到处都揭穿实情的话,在海丝特·白兰以外,许多人的胸上都要闪耀出那个红字来的。 小珠儿,这是海丝特给他的女儿取的名字,已经长大了。她天性聪明而任性,倔强而近乎狂野。 一天,海丝特带着女儿去州长的邸宅,塔尔文州长和几个当地的正统人士图谋把珠儿交给其他人监护。她决然要用自己的权力去争一下。 当时威尔逊牧师、丁梅斯代尔牧师以及那个青年牧师形影不离的罗格·齐灵渥斯医生都在场。州长严峻的目光盯着那个佩戴红字的人说,“海丝特·白兰,关于你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我们不能把一个孩子交给一个堕落在陷阱中的人来管。为了孩子的幸福,她应当离开你。” “上帝给了我这个孩子,”海丝特把珠儿用力搂进怀里,叫道,“她为了补偿你们从我身上所剥夺去的一切,把她给了我。她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苦恼。你们没有看见吗?她就是那个红字,她有千万倍的力量来赎偿我的罪恶,你们不能把她夺去,我情愿先死掉!” 那个老牧师说,“可怜的妇女,我们会好好的照顾这个孩子的。” “上帝把她交给我手里,”这个女人的声音提高得等于嘶叫,“我绝不会放弃她!” 她转身对着那个年轻的牧师,“你来替我说话!你从前是我的教长,你曾管束过我的灵魂,而且你比这些人们更理解我。我不愿意失掉这个孩子,你明白我心里有什么,你明白一个母亲的权利是什么!” 海丝特差不多要发疯了。青年牧师面色苍白,一手拢在心头上,每逢他受到震动的时候,照例总是如此。 “她的话里是含有真理的。”他说,“上帝给了她这个孩子,这个因父亲的犯罪与母亲的耻辱而生的孩子,要用许多的方法来感化她母亲的心,所以那位母亲才那么恳切的来申辩。她有保护她的权利。请你们相信我,她已经认识了上帝在这个孩子的存在上造出的神圣奇迹。她也能感到这个恩赐比什么都重要的用意,就是要这位母亲保持灵魂的活力,防止她向最黑暗罪恶的深渊里堕落。为了海丝特·白兰,也为了那个可怜的孩子,还是随天意安排,我们不要管吧。” 青年牧师这一番娓娓动听的道理,赢得州长和老牧师的赞同,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了。只有老罗格·齐灵渥斯不以为然地微笑着。 罗格·齐灵渥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就选中了丁梅斯戴尔先生做他精神的导师。那个时候,青年牧师的健康正开始衰退,医生的恰巧来到,使人们觉得有天佑的意思。因此,一方面,医生怀着强烈的兴趣,以一个教民的资格追随在他的左右;一方面,那些长老、主妇、牧师、修道女都恳求丁梅斯戴尔先生接受这位自告奋勇的医生的治疗。 就这样,老罗格·齐灵渥斯成了青年牧师的顾问医师。使医生感兴趣的不仅仅是病症,他更热心要探索的是病人的个性和气质。过了一段时间,丁梅斯戴尔先生的朋友们受了罗格·齐灵渥斯的示意,设法布置了一所房子,叫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这样好使牧师生命的脉息让他热心的医生一一入目。 可是自从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以后,人们发现他们所爱戴的牧师双颊也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消瘦,声音也比从前更颤抖了。他的手压在胸上,竟变成了经常的习惯。渐渐的有一种说法传了开来,说丁梅斯戴尔牧师遇到撒旦的使者装扮成老罗格·齐灵渥斯的模样来折磨他了。 牧师本人也朦胧地意识到,有一种与他为敌的东西闯进他的生命。医生十分敏感,每当牧师对他投射出惊恐的眼光,医生便坐下来,变成他的温存、爱护、同情的朋友,绝不再探寻他的隐私。 一天正午,牧师坐在椅子里沉睡起来。医生走进屋来,他把手放在他的病人的胸上,拨开从未曾解开过的法衣。 这时,丁梅斯代尔先生畏缩了一下,医生转身走开了。他露出的是一种疯狂的神情,惊异、欢喜、而又恐怖。 丁梅斯代尔牧师一面受着肉体疾病的痛苦,一面受着灵魂烦恼的折磨。他登上讲坛,不止一次的告诉他的教民, 他是最卑鄙的人群中的一个卑鄙者,是最坏的罪人,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邪恶的东西。但是听讲的人反而越发尊敬他,他们把他看成是一个超凡入圣的人。 他厌恶自己的虚伪,他在深锁的密室里用鞭子猛击自己,他绝食,甚至双膝颤抖,他不断地磨难自己,彻夜不眠,但是心灵仍得不到安宁。 五月初,一个朦胧的午夜,他梦游似的走到好久以前海丝特·白兰示众的那个绞刑台上,他站在那里,突然感到一阵极度的恐怖,仿佛全宇宙都在凝视着他那赤裸的胸膛,盯住了他心房上的那个红字的标记。 远处的一道微光正在迫近,他听到了脚步声,当灯光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看见了威尔逊牧师。威尔逊牧师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拽着他的黑袍,小心地望着脚下的泥泞。当灯笼的微光在远处消隐以后,丁梅斯代尔感到一阵昏迷。 蓦然又传来一阵尖锐响亮的笑声,那笑声叫他心里抖了一下,他辨别出那是小珠儿的声调。 “珠儿!小珠儿!”接着,他又放低了声音,“海丝特·白兰!海丝特!是你在那里吗?” 海丝特正领着珠儿回家,“是的,正是我,还有我的珠儿。” “上这儿来,海丝特,你,还有小珠儿。”牧师说着,“你们两个人从前都在这里站过,可是我没有同你们一起。再上来一次,我们三个人站在一道!” 海丝特·白兰默默地登上了台阶,手牵着小珠儿,牧师握着孩子的另一只手。就在这一瞬间,一股新生命的汹涌潮水如激流般注入了他的心胸。 “牧师,”小珠儿悄悄地说,“明天中午,你愿意同我和母亲站在这里吗?” “不;”牧师一阵颤栗,顷刻唤醒了那已经磨难他许久的恐怖,“我的孩子,总有一天,但不是明天,我会同你的母亲和你站在一起。” 珠儿固执地问,“在什么时候呢?” 牧师呐呐的说,“在最后审判的日子。” 牧师抬头仰望天顶,看见一个用暗红色的火线划成的巨大的字——A字,这其实是一颗流星。就在它照亮大地的那一刻,牧师看见珠儿正用手指着老罗格·齐灵渥斯,他就站在离刑台不远的地方。 “那是什么人,海丝特?”牧师恐怖极了,喘息着说,“我一见到他,灵魂就发抖,他是什么人?我恨他,海丝特!” 海丝特想起她的誓言,沉默了。 流星陨落之后,大地一片黑暗,医生已走近刑台脚下。 “虔诚的丁梅斯代尔牧师,果真是你吗?哦,真的不错!来吧,圣洁的先生,我亲爱的朋友,让我来领你回家吧。” 牧师顿时觉得像一个浑身麻木地从噩梦中醒来的人,全身直打冷颤。 海丝特·白兰自那晚以后,发现牧师的神经似乎完全毁坏了。她大为震惊,她觉得她对牧师有一种责任。她虽然与社会隔绝了联系,但她和牧师之间是两个罪人的联系,无论她或者是牧师都不能够切断。于是,她决心去会从前的丈夫,尽一切力量来解救那显然已经被他捉在手里的牺牲者。 海丝特·白兰在他采药的小路上找到了他。 “我要和你说一句话。七年前,当我被迫答应替你保守秘密的时候,就把他出卖了。自那天以后,你追踪着他,你搜索他的思想,你蹂躏他的心胸,你使他每天受罪。而他却不晓得你。” 罗格·齐灵渥斯问,“我对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呢?若不是我的帮助,他和你共同犯罪以后不出两年,他的生命便会在痛苦中烧毁了。他现在所以能够还趴在地上呼吸,完全是靠我的力量。” 海丝特·白兰说,“他还是马上死掉的好。” “他能够马上死掉倒是好的,”老罗格叫道,他内心里有一团鬼火从他的眼睛里发射出来。“上天没有赐给我饶恕的力量啊,我要他为着我的复仇和怨气而活着,要他忍受恐怖的噩梦与绝望的痛苦。” 海丝特·白兰明白眼前这个魔鬼绝不会放过可怜的牧师,她决定亲自去见牧师。她打听到牧师前天到印第安人的村落去了,大概在明天午后回来。因此,她带着珠儿去他回来必经的森林。她们走进森林深处,她打发珠儿一个人去小溪边玩儿,然后坐在一棵巨大的松树下默默地等候。 牧师走过来了,他慢慢地走着,差不多快走过去了,海丝特·白兰终于喊了出来,“阿瑟·丁梅斯代尔!”她的声音嘶哑, “谁?”牧师突然一惊。 “海丝特!海丝特·白兰!”牧师认出树荫下的人影,立即振奋起来。 “那个老人,那个医生,和你同居一个房子,人们管他叫罗格·齐灵渥斯的,他是我的丈夫!” 牧师看了他一眼,痛苦地跌坐在地面上,双手掩住面孔嗫嚅着,“我早该知道的!这件事有多么可怕!” 海丝特·白兰张开双臂抱住了牧师,把牧师的头紧扼在她的胸上,没留心牧师的脸正贴着那个红字,牧师想抽出身来,但是挣扎不开。面对牧师的怨愤的脸,海丝特·白兰不敢放开他,全世界都蔑视海丝特·白兰,长长的七年间,全世界都蔑视这个孤寂的妇人,她忍受了这一切。但是眼前这个苍白、衰弱、有罪、愁苦的人的蔑视,海丝特·白兰却忍受不了。 “你还能够饶恕我吗?”她一遍遍的反复着,“你可以不蔑视我吗?” “我一定饶恕你,海丝特,”牧师深深的叹了口气,“愿上帝饶恕我们两个,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那个老人的复仇,比我的罪恶还更黑暗!” 他们手握着手,并排坐在折倒的树干上。海丝特充满激情的劝说牧师漂洋过海,到一个看不见白种人足迹的地方去做自由人。牧师的心振奋起来了。海丝特·白兰提到,恰巧有一只船泊在港湾里,三天之后就要航行到英国去。海丝特·白兰认识那船的船长和水手,她可以秘密的替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弄到仓位。 而第三天,牧师恰要做一次庆祝选举的布道。他若想结束他的牧师生涯,再也寻不到比这更适当的方式和时间了。他好像看见了光明,一种奇异欢欣的火光闪耀在他的脸上。 海丝特·白兰看见精神焕发一新的他兴奋极了,解开红字的扣针,从胸上取下来,抛到远远的枯叶间。海丝特·白兰要把过去的一切全抛掉,开始新的生活。这时,她看见站在小溪对岸的珠儿,她招呼着她,但她却不应声,用她那双明亮不驯的眼睛,时而注视着母亲,时而注视着牧师,还摆着一副威严的气势,挺着小小的食指指着海丝特的胸膛,她的脸颊顿时苍白了。 她瞟了牧师一眼,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走向远处,捡起红字,重新扣在胸上,然后他伸出手,“孩子,现在你认识母亲了吧?” 珠儿跳过小溪,抱着母亲吻她的额头和双颊,还吻了她胸前的红字。 “为什么牧师在这儿?”珠儿问,“他爱我们吗?他肯和我们手牵着手一起回到市场去吗?” “现在不行,亲爱的孩子。”海丝特答道,用力把珠儿拉到牧师面前,牧师在他的额上接了一个吻,珠儿立刻挣脱母亲,跑到小溪边,弯下身子洗她的前额。 牧师从森林中回来之后,兴奋得不能自已。他拒绝了老医生的药物,大吃大嚼为他准备的食物。他通夜不眠,以奔放的思想和感情写他的选举说教文。 选举日那天,海丝特和小珠儿很早就到了市场上,那里早已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等着观看全部伟大的人物,州长、知事、牧师从这里经过。 海丝特在市场上碰见了她要搭乘的那只船的船长,船长说,“太太,我必须吩咐管理员在你预定的床铺以外多预备一个位置了。那位医生自称齐灵渥斯的,他说他是你的同伴,想同你们一起航行。” 海丝特心里非常惊慌,在这一瞬间,她瞥见老罗格·齐灵渥斯正站在市场的一角对她微笑。海丝特还没有考虑好怎样对付这种新局面,教堂里丁梅斯代尔先生说教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那声音时而甜蜜,时而庄严,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胸。 一会儿,声音停止了,一瞬间的沉默之后,人们狂喜的赞美牧师,他们认为从来没有过一个演讲的人像他今天这样,有过如此明智、如此崇高、如此神圣的精神。丁梅斯代尔先生到了一生中绝对胜利的光明时期。接着,海丝特听到音乐的鸣响与护卫队的整齐步伐声,走出教堂的门口,队伍要走向市政厅,去参加盛大的宴会。 一大串庄严而令人敬畏的父老们走进市场时,人们对他们欢呼致敬,他们的眼光特别注视着可以看见牧师的方向。突然,欢呼声沉息下来,变成悄悄低语。牧师在全然的胜利中看起来是多么衰弱和苍白呀,他踉踉跄跄走到刑台对面,在逝去的许多悲惨岁月以前,那里曾经站立怀抱着小珠儿的海丝特,而且她的胸上佩戴着红字。牧师悼词停住了,虽然庄严欢欣的乐声还在召他去赴宴会。但是,他停住了,他转脸对着刑台,伸出他的双臂。 他说,“海丝特,到这边来!过来吧,我的小珠儿!” 他注视着他们,脸色可怕,但同时充满胜利的神情。人们骚动起来,那些在牧师四周立着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们,震惊得那么厉害,他们眼看着牧师倚在海丝特的肩上,走进刑台,踏上台阶,他的一只手紧握着由罪恶而诞生的孩子的小手。牧师转脸对着那些尊严可敬的统治者,对着他的弟兄辈的神圣牧师,对着人民,他伫立在全世界之上,在永恒的法庭之前,申诉他的罪恶。 “新英格兰的人民,你们曾经爱过我!你们把我看作神圣!请看我在这里,一个世界的罪人!我终于站到我七年前应当同这个妇人一起站立的地方了。就是这个妇人的臂膀,在这可怕的瞬间,用她小小的气力搀我爬到这里来。看呐!她佩戴着的那个红字,你们全都畏惧它!但是在你们之间还站立着一个人,他的罪恶与耻辱的烙印,你们却未曾躲避过。看呐!看这一个可怕人的证据!” 他痉挛的用力扯开他胸前的牧师的饰带,那件东西显露出来了,一瞬之间,呆若木鸡的群众都集中视线在这怕人的奇迹之上。 牧师站在那里,面上泛着胜利的红潮,然后他倒在刑台上。海丝特稍稍把他扶起,让牧师的头靠在她的胸上。 “别了,海丝特!”牧师吐出最后一句话,便气息断绝了。 丁梅斯代尔先生死后不到一年,老罗格·齐灵渥斯也逝世了。根据他的遗言,他在此地和在美国的一份很大的财产,遗赠给了海丝特·白兰的女儿小珠儿。 但是在医生死后不久,佩戴红字的人就不见了,珠儿也跟着她走了。好多年没有她的消息,红字的故事逐渐变成了一个神话。 一天下午,人们看见一个身材细长、穿着灰色长袍的妇人回到了那间久没有人住的小茅屋里,胸前依旧佩戴着红字。 人们从那些送来的印着家世纹章的信件中知道,珠儿依然活在世上,已经结了婚,非常幸福,并且时刻都在想念她的母亲。 但对于海丝特,在新英格兰比在珠儿定居的异乡,有着更真实的生活。她的罪恶种在此地,她的哀愁种在此地,所以她要在此地忏悔。随着岁月的消逝,红字已不是一个引起世人轻蔑和嘲笑的烙印,而变成一个符号,使人哀伤,使人望着它升起又畏又敬的心理。 又过了许多年,在后来建筑国王礼拜堂旁边的那块坟地里,在一座深陷的老坟的附近,又结了一个新坟。新坟是在深陷的老坟附近,可是却隔着相当的空间。好像两个长眠者的尘骸是没有资格混在一起的。不过,两座坟合用一个墓碑,那上面刻着铭文—— “一片黑地上,刻着血红的A字。” |
〔红字〕霍桑/张家声
51t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杨和柳' 的评论 :
谢谢杨柳精彩的评语。
其实红字这本书,当年也是基本没有细读,看了个开头,只记得一个年轻的太太背负了罪名,要在胸前带着羞辱的红字,伴其一生。读起来很压抑,就赶快往后翻,快点“看完”好去借另一本。
这次做帖,才认真的体悟到年轻牧师因负罪而承受的心灵上巨大的煎熬,就连海丝特提出的移居海外开辟另一片生机的计划也被阴险的医生扼杀了。留给他的,只能是牵着所爱的人的手,向全城人袒露那一直折磨着自己的红字,“面上泛着胜利的红潮”,倒在了刑台上。
海丝特在多年的漂泊以后,回到新英格兰,活着,“但愿我能忍受住他的苦痛”,死了,也要用共同的墓碑,来祭奠他们共同拥有的刻着红字的人生。
谢谢杨柳精彩的评语。
其实红字这本书,当年也是基本没有细读,看了个开头,只记得一个年轻的太太背负了罪名,要在胸前带着羞辱的红字,伴其一生。读起来很压抑,就赶快往后翻,快点“看完”好去借另一本。
这次做帖,才认真的体悟到年轻牧师因负罪而承受的心灵上巨大的煎熬,就连海丝特提出的移居海外开辟另一片生机的计划也被阴险的医生扼杀了。留给他的,只能是牵着所爱的人的手,向全城人袒露那一直折磨着自己的红字,“面上泛着胜利的红潮”,倒在了刑台上。
海丝特在多年的漂泊以后,回到新英格兰,活着,“但愿我能忍受住他的苦痛”,死了,也要用共同的墓碑,来祭奠他们共同拥有的刻着红字的人生。
杨和柳 发表评论于
您的家像桌上斟了半碗清茶,读完,忍不住闲谈,一谈再谈。
杨和柳 发表评论于
抗压性,女人比男人强
***
很好玩。我在另一个海归跟帖里说过男人比女人抗压能力强。
回到海丝特和牧师。
牧师没活明白,他只是对他受教的理论情感充沛,慷慨激昂。
他没堪破他对海丝特的爱到底是来自邪恶的情欲还是真正的爱,所以,海丝特的丈夫,那个老男人,那个医生,在时时刻刻敲打、窥探的时候能利用他情感的软弱和对宗教教育、人生理解的不成熟,而一步步构陷成思想的深渊,杀他于无形。(尽管此简写里没说,我瞎猜)
本质上,牧师是真正地爱海丝特,尽管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爱,但是海丝特知道牧师给与她是满腔深情,所以她才有勇气一腔孤勇来保护牧师,并信守秘密。
真正的爱是不灭的火焰,能毁灭周遭的世界,但不能毁灭这个人。海丝特正是如此。
另外,海丝特了解那个医生,了解她的丈夫,因为了解和看透了,所以,哪怕妥协和委屈,并不能把刀插到她心里去,医生伤不了她。
再回到牧师,牧师跟海丝特的爱是否对等?未必。牧师爱海丝特,但是跳不出自身的局限。大部分时间做牧师的,不会是社会上的强者,他们或许是智者,但囿于对谋生的恐惧,做了伸手族。他不自信。我怀疑牧师是孤儿,或者寡母养大。
***
回归咱俩歧路,无论男女,抗压与否,取决于是否在自身的认识和处境上刚强壮胆。
***
很好玩。我在另一个海归跟帖里说过男人比女人抗压能力强。
回到海丝特和牧师。
牧师没活明白,他只是对他受教的理论情感充沛,慷慨激昂。
他没堪破他对海丝特的爱到底是来自邪恶的情欲还是真正的爱,所以,海丝特的丈夫,那个老男人,那个医生,在时时刻刻敲打、窥探的时候能利用他情感的软弱和对宗教教育、人生理解的不成熟,而一步步构陷成思想的深渊,杀他于无形。(尽管此简写里没说,我瞎猜)
本质上,牧师是真正地爱海丝特,尽管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的爱,但是海丝特知道牧师给与她是满腔深情,所以她才有勇气一腔孤勇来保护牧师,并信守秘密。
真正的爱是不灭的火焰,能毁灭周遭的世界,但不能毁灭这个人。海丝特正是如此。
另外,海丝特了解那个医生,了解她的丈夫,因为了解和看透了,所以,哪怕妥协和委屈,并不能把刀插到她心里去,医生伤不了她。
再回到牧师,牧师跟海丝特的爱是否对等?未必。牧师爱海丝特,但是跳不出自身的局限。大部分时间做牧师的,不会是社会上的强者,他们或许是智者,但囿于对谋生的恐惧,做了伸手族。他不自信。我怀疑牧师是孤儿,或者寡母养大。
***
回归咱俩歧路,无论男女,抗压与否,取决于是否在自身的认识和处境上刚强壮胆。
51t 发表评论于
回复 '杨和柳' 的评论 :
谢谢杨柳听读和留言。
对人格的羞辱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嗜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冲在额上被刺金字,走到哪里都是个“贼配军”;就是到了现代,服刑期满,出来后还是个“劳改释放犯”,这“犯”字永远如影随形。
就连敢于面对一切羞辱的海丝特,把那个带给她屈辱的A字扔去了河边,可在小女儿的注视下又捡了回来。
胸前有形的A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中刻下的那个无形的A字。海丝特挺过来了,牧师先生却没能挺过。抗压性,女人比男人强。
谢谢杨柳听读和留言。
对人格的羞辱一直是这个社会的嗜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林冲在额上被刺金字,走到哪里都是个“贼配军”;就是到了现代,服刑期满,出来后还是个“劳改释放犯”,这“犯”字永远如影随形。
就连敢于面对一切羞辱的海丝特,把那个带给她屈辱的A字扔去了河边,可在小女儿的注视下又捡了回来。
胸前有形的A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中刻下的那个无形的A字。海丝特挺过来了,牧师先生却没能挺过。抗压性,女人比男人强。
杨和柳 发表评论于
感谢推荐。我没读过红字。对这种痛苦和羞辱很震撼,也很感叹。作家在反思爱、复仇、背叛与精神控制。
看你做帖做了三天,辛苦了,任何坚持不懈、偏安一隅、默默坚守都令人敬重。
回到小说。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女的知道自己丈夫有外遇依然硬抗,装做不知道,因为家财万贯。直到其丈夫去世前,说:你的孩子跟情人的孩子大致同时期出生的,趁着你不注意,我把俩孩子换了,她对你的孩子很好,视如己出,你看在亲生子的份上,相信你一定会分财产给那个孩子。
估计这故事是编的,但一个男的,开始报复的时候,女的无法招架。正如海丝特的丈夫。这女的,为了财产,跟不爱的丈夫耗尽一生,最终还是一无所有。
胆寒。无爱的冷酷无情堪比行刑。
看你做帖做了三天,辛苦了,任何坚持不懈、偏安一隅、默默坚守都令人敬重。
回到小说。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女的知道自己丈夫有外遇依然硬抗,装做不知道,因为家财万贯。直到其丈夫去世前,说:你的孩子跟情人的孩子大致同时期出生的,趁着你不注意,我把俩孩子换了,她对你的孩子很好,视如己出,你看在亲生子的份上,相信你一定会分财产给那个孩子。
估计这故事是编的,但一个男的,开始报复的时候,女的无法招架。正如海丝特的丈夫。这女的,为了财产,跟不爱的丈夫耗尽一生,最终还是一无所有。
胆寒。无爱的冷酷无情堪比行刑。
51t 发表评论于
好长时间没有听长篇了,来个长的。没时间听或是耐不住长时间听的,慎入。
这是《红字》的缩写本,自然没有原著的精彩,好多细节描写不可能包括,但原著是长篇小说,不可能做成帖子,听听缩写本,也是不错了。
做这种帖子,费老劲了,断断续续的花了三天时间才弄成这样,音频部分倒在其次,主要是文字部分,但既是自己要做,就不要抱怨,大体完成后,从头到尾一听,有点意思,也有一小点喜悦感。
这些世界名著,中学时接触过,那时我们的一个混友搞到了一批名著(估计是偷的),堆放在他家里,我们去登个记,就可借一本拿回家看。一是排队者多,快看完好拿下一本;二一个,估计大家心知肚明,说不定哪天派出所上门就给吞没了,啥也看不了了,所以都是囫囵吞枣的快看,算是留了个大体印象。这次做帖子,把浅浅的印象加深了不少,也算是有了一点小收获。
这是《红字》的缩写本,自然没有原著的精彩,好多细节描写不可能包括,但原著是长篇小说,不可能做成帖子,听听缩写本,也是不错了。
做这种帖子,费老劲了,断断续续的花了三天时间才弄成这样,音频部分倒在其次,主要是文字部分,但既是自己要做,就不要抱怨,大体完成后,从头到尾一听,有点意思,也有一小点喜悦感。
这些世界名著,中学时接触过,那时我们的一个混友搞到了一批名著(估计是偷的),堆放在他家里,我们去登个记,就可借一本拿回家看。一是排队者多,快看完好拿下一本;二一个,估计大家心知肚明,说不定哪天派出所上门就给吞没了,啥也看不了了,所以都是囫囵吞枣的快看,算是留了个大体印象。这次做帖子,把浅浅的印象加深了不少,也算是有了一点小收获。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