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icholas Wade 翻译by志愿者 投稿 陌上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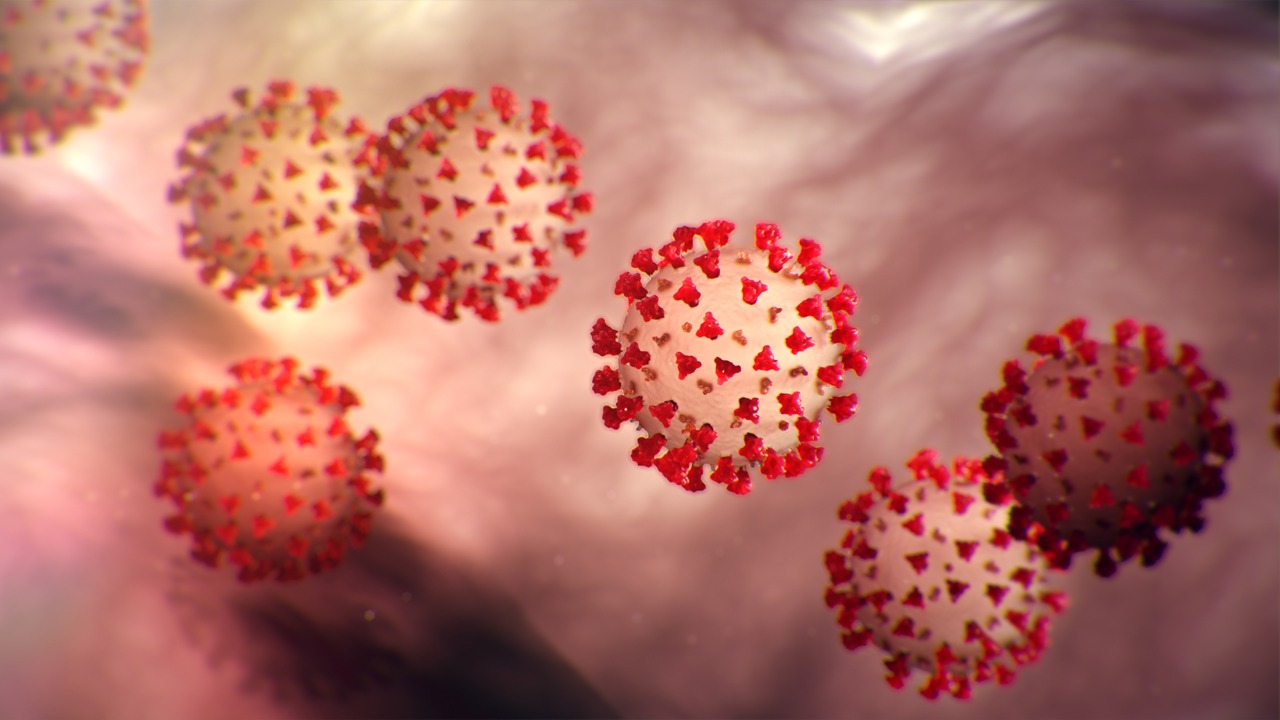
欢迎转载,请注明来自陌上美国电报频道:https://t.me/MoshangUS
庚毒探源,顺藤摸瓜 (上)
——是人还是自然打开了武汉的潘多拉盒子?
作者:Nicholas Wade(尼古拉斯·韦德)
(作者简介:尼古拉斯·韦德是著名的英籍作家和科技新闻记者,1942年出生于英国,1964获英国剑桥大学自然科学学士学位。他1967年到1971年间作为科学作家和编辑服务于《自然》杂志。1970年移民美国后从1972年到1982年在《科学》杂志工作了10年。他1982年始加入《纽约时报》,作为其下属的《科学时报》的专职作家和编辑工作了30年,直到2012年退休,之后还作为自由作家经常为《纽约时报》撰稿。)
庚毒在全球肆虐已超过一年,死亡人数将很快达到300万人。然而,庚毒的来源至今不确定:政府和科学家的政治动机让此事蒙上阴翳,而主流媒体似乎也无助于澄清。
我将在本文通过对已掌握的科学事实进行梳理。这些事实对所发生的事情提供了许多线索,并为读者提供了自我判断的证据。 然后,我们将尝试谈谈应该由谁来负责这个复杂问题,虽然首先要谈及中国政府的责任,但责任远远不限于中国。
看完本文后您可能会学到很多有关病毒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我尽量避免读者在阅读中感到痛苦,但必要的科学解释是必须的,因为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科学仍是引领我们穿过迷宫的唯一确定的线索。
引起疫情的病毒的正式名称叫SARS-CoV-2,但可以简称SARS2。众所周知,关于庚毒起源有两种主要说法,一是自然地从野生动植物跃迁到人体,二是该病毒从实验室逃逸。 如果我们希望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弄清病毒来源事关重大。
我将分别介绍两种起源理论及其合理性,然后看哪种理论能对已知事实提供更好的解释。必须指出,迄今为止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获得直接的证据。每种说法都取决于一组合理的假设,但均缺乏实锤证据。 因此,我目前仅有线索而无结论,不过这些线索都指向一个特定的方向。 在此方向的推断下,我将从这场灾难性的乱麻中勾勒出一些基本轮廓。
新冠疫情于2019年12月首次爆发后,中国当局报告称在武汉的一个菜市场(一个出售野生动物肉类的地方)发现了多个病例。 这使专家们想起了2002年SARS1疫情,在该次疫情中首先是蝙蝠病毒传给了在菜市场出售的果子狸,然后从果子狸传播给人类。2012年的MERS疫情也是由类似的蝙蝠病毒引发,那次的中间宿主是骆驼。
病毒基因组的解码显示,SARS2属于β-冠状病毒家族,SARS1和MERS病毒也是该家族的成员。这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SARS2和SARS1和MERS病毒一样,也是一种天然病毒,它成功地从蝙蝠通过某个中间宿主动物跃迁到人身上。SARS2与菜市场相关、与SARS1和MERS病毒类似这些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中国科研人员在武汉发现了早先与菜市场毫无联系的病例。 可是很快在一片期待支持自然发生论证据的形势下,这个事实似乎被人有意忽视了。
不过,武汉毕竟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所在地,而此研究所是世界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 所以,不能排除SARS2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我们有两个有关病毒起源的合理解释。
在疫情初期,公众和媒体对病毒起源的舆论就被两个科学机构发表的支持自然起源说的严正声明所影响。这些声明在发表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
某些病毒学家等人在2020年2月19的《柳叶刀》上声明道:“我们共同强烈谴责COVID-19是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而当时断言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为时过早。 他们说,科学家“无可置疑地得出了结论,认为该冠状病毒就是起源于野生动物”,并强烈呼吁读者与中国同行共同站在抗疫的前线。
其实认为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意思是指因事故所致而非由阴谋所致,这与声明者的说法恰恰相反。这当然是件需要研究的事,而非一味拒绝它。优秀科学家的一个标志是,他们应不遗余力区分自己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 按此标准,在《柳叶刀》上签名的这些科学家是些不称职的科学家:他们向公众保证了他们自己也不确定的事情。
后来发现《柳叶刀》这封声明信是由纽约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 of New York)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组织和起草的。是Daszak博士所属的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研究。 如果SARS2病毒确实是从他资助的研究中项目中逃逸的,那么Daszak博士可能会被入罪。他对 这个严重的利益冲突非但没有向《柳叶刀》的读者披露,相反,在该信的结尾写道:“我们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究竟谁应该对庚毒的流行负责这个问题,对Daszak博士这样的病毒学家来说利益攸关。在20多年大多数时间中,他们一直躲避了公众关注在玩一个危险游戏。他们在实验室中不断地制造一些比自然界中存在的病毒更危险的病毒。他们的说辞是他们可以安全地操作,并且通过走在自然界前面研究出新病毒,他们可以预测和防止病毒的“溢出”,即从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类。 如果SARS2真的是从这类实验室逃逸的话,那将造成一场恐怖的反弹,公众的义愤风暴将影响世界各地的病毒学家,而不仅仅限于中国。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编辑安东尼奥·雷加拉多(Antonio Regalado)于2020年3月表示:“这将从上到下彻底颠覆科学大厦。”
在塑造公众意见方面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声明是2020年3月17日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信(也就是说,这是一篇观点陈述而非科研文章)。 它的作者是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为首的几位病毒学家。 这五名病毒学家在该信函的第二段中宣称:“我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SARS2病毒不是实验室的建构,也不是被有意操纵的病毒。”
不幸的是,按照我们上面的定义,这也属于低劣科学的一种情形。对病毒基因组进行剪切和粘贴的老方法的确会留下明显的人为痕迹。 但是,被称为“看不见”(no-see-um)或“无缝”(seamless)的新方法确可以在剪切和粘贴中不留任何痕迹。其它一些处理病毒的方法也可以不留痕迹,例如所谓连续传代技术(serial passage),即将病毒反复从一个细胞培养基转移到另一个细胞的技术。 如果某个病毒被认为操作了,无论是通过“无缝”法或“连续传代”法,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知道该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的。Andersen博士及其同事其实是在向读者担保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事情。
该信的讨论部分是这样开头的:“ SARS2不太可能在实验室中通过操控与冠状病毒SARS-CoV相关的冠状病毒而获得”。不过拜托等等,该信开头不是说SARS2很清楚没有受到操控吗? 信件的作者在开始推理时,其确信度似乎下调了好几个等级。
一旦在论证中引入了技术语言,确信度立刻就下降了。作者提出了两个论证人为操控不可能的理由,但哪一个也无法确定。
首先,他们论证说SARS2的刺突蛋白与人的受体目标ACE2虽然结合得很好,但是该方式与物理计算所得到的最优结合方式并不同,所以该病毒一定是通过自然选择而非通过人工操作而产生的。(译者按:意思是如果是人工操控的话,其结合方式一定按最优计算方式进行)
如果你觉得这个论证难于理解,那是因为该论证过于牵强附会。作者的基本假设是(虽没有明确说明),只存在唯一一种方式(人工计算)让蝙蝠病毒与人体细胞结合,即首先计算出人类受体ACE2与病毒入侵的刺突蛋白之间的最强拟合方式,然后他们根据此计算来设计该刺突蛋白(通过选择构成刺突蛋白的氨基酸单元序列)。该论文说,由于SARS2的刺突蛋白与计算的最优设计由差异,所以它没有被操纵。
但以上说法是对病毒学家将刺突蛋白与选定靶标进行结合的实际方式的无视。刺突蛋白与靶标的结合并不是通过计算进行的,而是通过将刺突蛋白从其它病毒中进行基因剪接获得,或通过连续传代(serial passage)来完成的。对于连续传代方式,每次将病毒的后代转移到新的细胞培养物或动物上,从中选出较为成功的后代,直到出现与人类细胞紧密结合的蛋白。所有繁重的工作其实是通过自然选择完成的。Andersen等人的文章中所说的通过计算来设计病毒刺突蛋白的推测,与该病毒是否被以上两种方法所人工操纵完全无关。
信件作者反对人工操控的第二个论证更加牵强。尽管绝大多数生物的遗传物质是DNA,但许多病毒使用的是DNA的化学近亲RNA来实现遗传。不过RNA很难操控,所以基于RNA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人员会先将RNA基因组转换为DNA序列,然后在转换后的DNA版本上进行增改操作,再将修改后的DNA基因组转回传染性的RNA。
科学文献中对DNA骨架的描述只有若干种。Andersen小组说,任何操控SARS2病毒的人都“有可能”采用了其中某个已知骨架。因为SARS2并不源自这些骨架,所以不存在人工操控。但是这个说法显然没有定论,因为DNA骨架非常容易制作,因此很可能使用从未公开的DNA骨架来操控SARS2。
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Andersen小组提出的两个论点,用以支持他们宣称SARS2病毒显然未被操控的声明。虽然他们结论完全基于两个毫无定论的猜测,可他们却让全世界的新闻界深信不疑,SARS2不可能从实验室逃逸。有篇技术分析文章毫不留情地驳斥了Andersen的这个说法。
科学应该是个自我纠错的专家社区,其中科学家不断互检彼此的工作。可是为什么没有其他病毒学家指出Andersen小组充满了荒谬论证的漏洞呢?也许是因为当今在大学中发表不同的观点代价可能是及其昂贵的。你可能会因为论点出格而丧失工作。如果某位病毒学家敢于挑战本领域官宣的观点, 那么他下次申请研究经费时,可能就会被负责政府研究经费分配的专家委员会拒绝。
Daszak和Andersen发表的公开信具有十足的政治性而非科学陈述,但其效果令人吃惊。主流媒体反复发文说,专家们的共识已排除了病毒从实验室逃逸的可能性。这些主流媒体作者的主要依据就是Daszak和Andersen的这两封信,可他们对信中的巨大论证漏洞却完全不懂。主流媒体以及主要网络媒体都配有专职的科学记者,这些科学记者理应能够对科学家提出质疑并对其观点进行审查。可是Daszak和Andersen的声明却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对病毒自然涌现说的疑问
直到2021年2月左右以及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个委员会造访中国之前,病毒的自然界涌现说一直是媒体所喜爱的理论。WTO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和进入实验室受到了中国当局的严格控制。其成员也包括无所不在的Daszak博士,他们在访问前、访问期间和访问后一直肯定病毒极不可能从实验室逃逸。但这个说法并不是中国当局所希望见到的宣传上的胜利。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没能向该委员会提供支持自然涌现说的证据。
这很令人吃惊,因为无论是SARS1还是MERS病毒,都能在环境中找到大量痕迹。在SARS1疫情爆发后四个月内就确定了中间宿主,在MERS爆发后的九个月内就确定了中间宿主。然而,SARS2病毒大流行之后已经过了15个月,虽然经过大规模搜索,中国科研人员仍未找到该病毒的原始蝙蝠种群,也未找到SARS2病毒传给人体的中间宿主,也找不到任何血清学证据来证明任何包括武汉在内的中国人群曾在2019年12月之前接触过该病毒。自然涌现说到目前仍是一种假设,无论起初提出该假说的理由是否合理,事实是一年多来没有找到丝毫支持的证据。
如果一直找不到支持自然涌现说的证据,就应该认真考虑换一个假设,即SARS2病毒就是从实验室逃逸的。
为什么会有人想制造一种能够引发瘟疫流行的新型病毒?自从病毒学家获得了操控病毒基因的工具以来,他们就认为可以通过研究某种动物病毒跃迁到人类的可能性来预测潜在的病毒流行。病毒学家声称,在实验室中增强危险的动物病毒感染人类的能力是合理的。
以这个理由,他们重新建构了1918年的流感病毒,展示了如何从已发布的DNA序列来合成几乎已经灭绝的小儿麻痹症病毒,并将一个天花基因植入一个相关的病毒中。
这些加强病毒传染力的实验,通常被称为功能获得性实验(gain-of-function experiments)。 对于冠状病毒而言,刺突蛋白尤其令人感兴趣,刺突蛋白会在病毒的球形表面四处突起并大致决定了它的靶向动物种类。 例如,在2000年,荷兰研究人员对小鼠的冠状病毒刺突蛋白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只攻击猫,从而成了老鼠的幸事。
在发现蝙蝠的冠状病毒既是SARS1的起源,也是MERS的起源后,病毒学家才开始认真研究这类病毒。研究人员特别想了解的是,蝙蝠的刺突蛋白究竟需要发生什么变化才会感染人类。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蝙蝠病毒的首席专家、人称“蝙蝠女”的石正立的领导下,经常前往中国南部云南的蝙蝠洞探险,并收集了约一百种不同的蝙蝠冠状病毒。
然后石博士与北卡罗来纳大学著名的冠状病毒研究者Ralph S. Baric进行合作。他们的工作集中于增强蝙蝠病毒攻击人类的能力,为的是发现冠状病毒大规模流传的潜能(即感染人类的潜在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于2015年11月构建了一个新型病毒,其方法是使用SARS1病毒的骨架并用一种蝙蝠病毒(SHC014-CoV)的刺突蛋白来取代其刺突蛋白。这种制作出来的病毒可以感染人的呼吸道细胞,起码可以在实验室中感染呼吸道细胞的培养基。
这种由SHC014-CoV的刺突蛋白加SARS1骨架的病毒被称为嵌合体(chimera),因为其基因组包含两种病毒的遗传物质。如果SARS2病毒确实是在石博士的实验室中制造的话, 则其直接的原型就是SHC014-CoV/SARS1嵌合体,其潜在危险引起许多观察者的关注,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 in Paris)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Simon Wain-Hobson)说:“如果该病毒逃逸了,没有人能够预测其流行轨迹。”
Baric博士和石博士在其论文中虽然提到存在明显的风险,但认为应考虑该研究能够预测病毒跨种跃迁的好处。他们写道,科学审查小组“可能会认为这类基于已经流行的毒株而构建的嵌合体病毒太危险而不应进行”。他们认为,鉴于对功能获得性(GOF)研究的各种限制,事情已经“进入了GOF研究所关注的十字路口;必须要权衡两方面的风险,一方面是应对和缓解未来可能爆发的病毒,另一方面是制造了更多的高风险病原体。在制定未来政策时,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些研究数据的价值,以及此类的嵌合型病毒研究,考虑到其固有风险,是否值得继续进行下去。”
以上声明是在2015年发表的。从2021年往回看,可以说,获得功能研究(GOF)在预防SARS2流行上的价值为零。如果SARS2病毒确实是在功能获得性实验中产生的,那么可以说,该风险是灾难性的。
(待续)
联系方式:
电报频道: https://t.me/MoshangUS
社区建设群:https://bit.ly/35Jtpak
教育生活群:https://bit.ly/3fs7FFR
YouTube:https://bit.ly/3pKShXu
推特:https://twitter.com/MoshangUsa
原文链接:
https://nicholaswade.medium.com/origin-of-covid-following-the-clues-6f03564c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