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2/17(网图)
【George Smith】

The Epic of Gilgamesh有多个英文版本,我手上拿的是英国企鹅Penguin出版社的N.K. Sandars译本,现在最权威的当属英国伦敦大学Andrew R. George的企鹅新版本。
但说到The Epic of Gilgamesh英文翻译,不得不提到The Epic of Gilgamesh英文翻译第一人George Smith,因为正是他从大英博物馆在中东考古海量文字瓦片中发现了The Epic of Gilgamesh史诗Tablet 11 -Babylonian 洪水的故事,让古苏美尔文化在沉寂4000多年后重现天日。Gilgamesh史诗中洪水的故事,伊甸园的情节,与圣经挪亚方舟及亚当和夏娃的故事非常相似,而Gilgamesh与Enkidu的生死之情跟荷马史诗Iliad中Achilles与Patroclus基本雷同,就是Gilgamesh去寻找Utnapishtim的一路经历,就是荷马版奥德赛。George Smith的这一发现确实震惊世界,让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圣经和古希腊罗马文明。
由洪水的tablet开始,George Smith又三次去Mesopotamia考古,逐步挖掘出最早的文学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并相对精确地把它从古楔形文字翻译成英文。
可怜的是George Smith,他的考古学家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在他36岁时,就死在第三次考古回英国途中,留下妻子和6个还很小的孩子们。
George Smith – 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Assyriologist)
George Smith 1840年3月28日出生在伦敦Chelsea的一个贫穷的工薪家庭,在14岁时,他的父亲把他送到Bradbury and Evans出版社那儿当Banknote雕刻学徒工,很快,他的雕刻水平就脱颖而出。
但George Smith从小就对Mesopotamia古文化与历史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他做雕刻工的出版社在伦敦Russell Square附近,中午90分钟的休息时间里,他就快步走路到大英博物馆中东馆里—也就是当时我当时所在的中东和伊斯兰世界展区里研读他所能读到的古楔形文字及Mesopotamia考古展品;并且在学徒期间利用所有能找到的资源用一本字典自学古楔形文字,历史,和文化。
其实早先George Smith到大英博物馆来完全是出于对圣经研究的兴趣,只不过在免费的大英博物馆里,他发现了Mesopotamia古文化这一大的天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走上专业Assyriologist的道路。
大英博物馆在当时,只有三天对外免费开放,因为图书馆Trustees认为:大量没有受教育的工人阶层进来博物馆,只能破坏文物;博物馆的文物应该仅限于艺术学院的学生或其它特约人员。到现在为止,伦敦另一家学院附属埃及博物馆星期一也只能预约参观,除了其它时间免费。
英国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Assyriology还是个很生疏的行业,尽管前二十几年,考古学家从中东带回来了成千上万的瓦片,但并没有多少人能读得懂古楔形文字;而且,不光是要会读,而且要会拚瓦片,因为瓦片都是碎片,要知道哪些瓦片是可以拚到一起的,就象现在的拚图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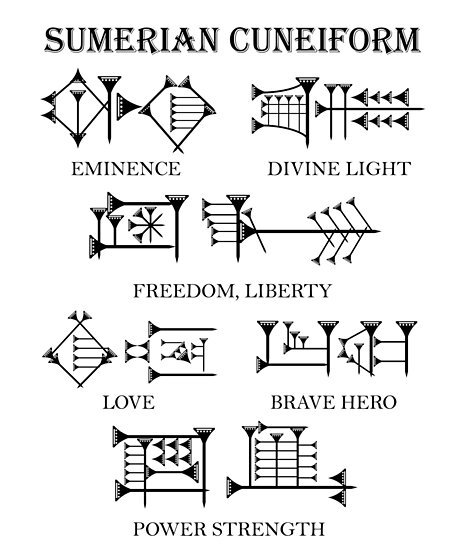

成年累月的自学,加上从来不缺的耐心和注重细节的品质,到George Smith20出头时,他的古楔形语言文字水平在英国已达到比较高的水平。
其实,大英博物馆中东馆的人早已注意到这个数年如一日总是来的小伙子了。当时,博物馆还是能够做到最大限度地容忍那些没有学术背景的人前来免费参观;但最后,当埃及馆的牛津学者Dr. Birch and Coxe of Balliol发现George Smith古楔形文字阅读水平甚至在他们这些专业人士之上后,就把他介绍给最早解读出古楔形文字的权威Rawlinson那儿。

Rawlinson发现,George Smith不光有非常专业的古楔形语言文字水平,而且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和高超的拚破碎写着古楔形文字瓦片的能力。Rawlinson强烈建议大英博物馆招收George Smith,因为在中东馆藏里,成千上万的残碎瓦片等着懂行的人归类和整理呢。
象做梦一样,George Smith走上了一条维多利亚时代低层工人家庭孩子所不能走的道路:正式成为大英博物馆的专业工作人员。
对新的工作,George Smith非常喜欢。George Smith充分利用这一工作岗位,全方位地提升他的古楔形语言文字水平,并开始有所有价值的发现。如1866年,他准确地识别出Assyrian inscriptions(亚述文字)中提到的希伯来君主,并为以色列历史的年表的准确性提供了新的细节。
George Smith还有个最为可贵的品质就是他能够不断地修改和完善他的考古发现。就象在他的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 一书的最后所说的:I have changed my own opinions many times, and I have no doubt that any accession of new material would change again my views respecting the parts affected by it…for certainly in cuneiform matters we have often had to advance through error to truth.
对George Smith越来越展现的才华与价值,Rawlinson建议博物馆让Smith成为他的助理,跟他一起共同完成Cuneiform Inscriptions章节。
George Smith对自己能走到这一天也充满自豪。他说:从1867起,我正式进入了专业的职业生涯,可以正规地研究古楔形语言文字了。但他始终感谢Rawlinson,因为没有Rawlinson的慧眼识人与打破传统偏见破格录取,他无缘进入大英博物馆这一专业领域。
George Smith – 发现大洪水(Flood Tablet)的故事

George Smith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条件跟现在不同。当时大英博物馆禁止使用汽油灯类,以防大火,在冬天阴郁的天气里,有时就给员工放假了。在工作的时候,George Smith就凭从窗户里照进来的阳光认真处理着被千年层渣遮挡的clay。
有一天,George Smith在大英博物馆二楼对着Russell Square(在这广场差点被松鼠攻击,大家小心,不要喂食松鼠,松鼠现在已养成看到人就索食的习惯)的窗台工作的时候,他站起来要去寻找一个瓦片,因为那个瓦片上有段文字可能可以证明圣经中洪水的故事,没想到却发现了古代Mesopotamia洪水(有时称巴比伦洪水)的事件:上面记载着风暴,大水,船只,停在山头,完全就是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
Red in tooth and claw.
A thousand types are gone;
I care for nothing,
All shall go.
George Smith知道,他面临着划时代的发现。据当时的工作人员说:他处于极度亢奋之中,甚至把衣服都脱了。George Smith说:I’m the first man to read that after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of oblivion!(经过两千多年的遗忘,我是第一个读到它的人!)
这一发现实在太震动了,用举世震惊来说明一定都不夸张。伦敦时报对这一消息也是头条报道。当新闻发布会开始时,当时的英国首相William Gladstone也来了。用现代The Epic of Gilgamesh权威,英国伦敦大学Andrew R. George教授的话来说: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首相前来参加巴比伦文化新闻发布会呢。
英国首相在会上说:the new discoveries in Mesopotamia, not so much for their relevance to the Bible but for give “a solidity to much of the old Greek traditions which they never before possessed. ”它将人们对荷马史诗的阅读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荷马“as the friend of my youth, the friend of my middle age, the friend of my old age, from whom I hope never to part as long as I have any faculty of breath left in my body”
英国首相激动人心的发言,让在场的人鼓掌欢迎经久不息。
其实,当时中东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考古也成为另一个战场。比如说,拿破仑征服中东时,带了170多个考古学家前往,是法国先发现和拥有Rosetta Stone(罗塞塔石碑)的,但它现在落在大英博物馆手里。
在西方,西方人是在荷马史诗的影响下成长的。英国首相William Gladstone退休后还写了一本关于荷马史诗的作品,以前提及的T.E. Lawrence也曾跟George Smith一样,因为杰出的文字语言才能,被大英博物馆录用,在1910-1914年间在中东Carchemish一带考古。T.E. Lawrence去世前几年,还成功地翻译出了荷马史诗《奥德赛》。
George Smith的新发现,包括Alice’s Adventure in the Wonderland的作者新教派Lewis Carroll也把伦敦时报的报道剪裁下来,放到自己的绘画作品里。
只不过,William Gladstone,T.E. Lawrence和Lewis Carroll都是牛津等名校的高材生,唯有George Smith,这个最主要的发现人,只是个靠着大英博物馆免费开放的便利自学成家的学者。
George Smith – 昙花一现的职业生涯
George Smith职业生涯,前后加起来可能只有十年。在第三次考古的时候,因疟疾感染在中东Aleppo去世。
因为George Smith的发现,包括他自己和整个国家,需要他发现更多,他先后三次前往中东考察。
在George Smith前往中东时,就发现他整体知识的缺失了,因为他不懂当地语言,也不懂如何与土耳其官方打交道,如行贿,他的考古工作举步维艰。
其实,在他第二次考古回来后,他已出版了六本考古发现书籍了,但当第三次博物馆派他再去时,当时中东一带已疟疾横行,多处处于战争状态,他曾提出提前结束工作回来,但他收到的博物馆秘书冷冰冰的信件,让他继续留着,无视他已病得奄奄一息。
其实,英国当时那个社会,对出生卑微靠自学成才者,其态度从博物馆秘书的信件就可看出。当时人们质疑博物馆秘书,他敢这样写件给其它学者吗?不敢,绝对不可能。
在大英图书馆Additional Manuscripts-39,300档案里,记录了Parsons医生所写的George Smith最后的日子。当时,在高温下,他连床都没有,没水喝,也没饭吃,躺在地板上,他失职的助手不在身旁。前三天,他还在继续修改手稿,写下日记。
当时George Smith写给大英博物馆的最后一封信已失踪了,但还保存着博物馆秘书冷冰冰的信件。到现在我们去英国图书馆时,还可查到。
去英国之前,在网上办理了大英图书馆的阅读卡,就是想一睹原始资料,可惜圣诞节期间开门时间太少了,并且心存不忍,没有成行。
George Smith在给妻子的信上是这样写的:Trust me I will fall on my feet wherever I am thrown, and I am determined I will not incur any more worry for people who do not deserver it.
George Smith的早逝是英国Assyriology行业的巨大损失,也是他家庭的惨重损失。他去逝后,留下了他的妻子和六个年幼的孩子。

其实,George Smith是个非常热爱家庭的人。在他写给妻子的信里,有些语句现在读来惨不忍睹。他希望妻子能到博物馆看他带回来的瓦片,因为没有她,他做的这一切都毫无价值: "I have all sorts of treasures, historical, mythological, architectural &c&c. I expect to bring home from 3,000 to 4,000 objects, you must come to the Museum and see them, it will be nothing to me if you do not share my success. ";他觉得他结婚太早了,无法过一个单身男人的生活,他需要妻子和他的孩子们。
George Smith的早逝举世轰动,整个社会也对他的家庭有着无限的同情;最后,维多利亚女王同意每月给George Smith一家每月150英镑的抚恤金,这多少也可让George Smith稍微宽心了。
当我们今天读到The Epic of Gilgamesh时,让我们还记得George Smith,他的早逝的生命;因为没有他的发现,这本书还不知什么时候重昭天日呢?正是基于他的发现,后来的考古学者才能逐步完善这部作品,并继续推动对中东古文明的发现和研究。
The Epic of Gilgamesh的完善是多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尽管它是个很薄的小册子,但其内涵朴素丰富的人生哲理,至今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The Epic of Gilgamesh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仅证明了Mesopotamia一带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证明了圣经和荷马史诗,都是Mesopotamia文明的传承。
在订2018年计划的时候,本想把这本书翻成中文,但并没有成功;但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和享受这部作品。
我很钦佩那些曾经为Mesopotamia文化研究付出时间甚至生命的人,是他们让我们今天还可以读到人类文明源头的作品;还可以追本溯源,一窥人类历史发展的脉络。
也深深感谢伦敦的众多免费博物馆。它不光是一个好去处,而且也让我在参观的时候感慨万千:如果在我们小的时候,生活中有这样的博物馆,我们这些人中,有的人的生活轨迹也许会重写,就象George Smith当时一样。


最后,还记得圣诞节后第二次去大英博物馆时,有个小孩子由妈妈带着拿着一张纸来寻找我正在看的the Standard of Ur, 他肯定没有仔细地看盒子上的图画,以为找到了。蹲下来跟他说:你可以转到盒子后面去,看看有什么不同。the Standard of Ur木盒子镶嵌着马赛克壳,盒子有两面:一是“战争”,一是“和平”(宴会场面)。你现在看到的是"战争",而纸上要求你找的是"和平"。
在陌生的小孩身上,尽管我只看到了一个寻常的孩子在完成任务;但站在中东博物馆里,我还是能感受到140年前的George Smith,一个充满知识饥渴异于常人的天才Assyriologist曾在这儿驻留多年的气息。
(待续)
